|
еҺ»е№ҙдә”жңҲпјҢеҠүе°Ҹжқұеҗ‘дҫҜе°ҺжҸҗеҮәгҖҠйҮ‘еҹҺе°ҸеӯҗгҖӢжӢҚж”қиЁҲз•«пјҢдҫҜе°Һ當дёӢе°ұжұәе®ҡз”ұжӮЁж“”д»»еҹ·иЎҢе°Һжј”пјҢдёҰиә«е…јж”қеҪұгҖӮе•ҹзЁӢеҲ°йҮ‘еҹҺйҖІиЎҢжӢҚж”қеүҚпјҢе°Қж–јеҪұзүҮзҡ„дё»и»ёжңүз„ЎеҲқжӯҘжғіжі•пјҹдәӢе…ҲеҸҲеҒҡдәҶе“ӘдәӣеҠҹиӘІпјҹиіҲжЁҹжҹҜдәҰжӣҫжӢҚйҒҺд»ҘеҠүе°ҸжқұзӮәйЎҢзҡ„зҙҖйҢ„зүҮгҖҠжқұгҖӢпјҢжӮЁжңүз„ЎзңӢйҒҺпјҹ
е§ҡе®Ҹжҳ“пјҲд»ҘдёӢз°ЎзЁұе§ҡпјүпјҡе…¶еҜҰйӮЈжҷӮеҖҷйғҪеҫҲйҷҢз”ҹпјҢйӣ–然иӘҚиӯҳеҫҲд№…пјҢдҪҶдёҚжҳҜдёҖиө·з”ҹжҙ»йҒҺпјҢиҖҢдё”д»–еңЁеҢ—дә¬пјҢдёҚйҒҺе°ұжҳҜжңүжҷӮзў°йқўпјҢеҗғеҖӢйЈҜгҖӮжҺҘжӢҚйҖҷеҖӢжЎҲеӯҗпјҢй«ҳиҲҲзҡ„жҳҜеҸҜд»ҘзңӢдёҖеҖӢ畫家畫畫пјҢеҲ°еә•иҰҒжӢҚд»ҖйәјйӮ„дёҚжҳҜеҫҲжё…жҘҡгҖӮи·ҹжӢҚзҡ„йҒҺзЁӢдёӯпјҢжҲ‘еҖ‘д№ҹе№ҫд№ҺдёҚжәқйҖҡд»Җйәји·ҹзүҮеӯҗжңүй—ңдҝӮзҡ„жқұиҘҝгҖӮе°Қж–јйҖҷеҖӢзүҮеӯҗзҡ„ж§ӢжғіпјҢиҰҒеҲ°ж•ҙеҖӢжӢҚе®ҢеӣһеҸ°зҒЈд»ҘеҫҢгҖӮзҙҖйҢ„зүҮе…¶еҜҰжҳҜеҫһеүӘжҺҘжүҚй–Ӣе§ӢпјҢеүҚйқўе°ҚжҲ‘дҫҶи¬ӣеҘҪеғҸйғҪжҳҜеңЁи’җйӣҶиіҮж–ҷгҖӮ
иЎҢеүҚеҸӘжңүзңӢдәҶд»–зҡ„дёҖдәӣиғҢжҷҜпјҢеңЁз¶ІдёҠиғҪжүҫеҲ°зҡ„гҖӮгҖҠжқұгҖӢжҲ‘д»ҘеүҚзңӢйҒҺпјҢд№ҹжңүйҖҷеҖӢзүҮеӯҗпјҢжҲ‘жңүжҠҠе®ғеё¶и‘—пјҢдҪҶеё¶еҺ»зөӮ究д№ҹжІ’зңӢгҖӮеҸҚиҖҢжҳҜеүӘжҺҘе®ҢеҫҢжҲ‘жңүзңӢйҒҺдёҖйҒҚгҖӮйӮЈйғЁзүҮ當жҷӮйӮ„еңЁжҲ‘зҡ„иЎҢжқҺз®ұиЈЎйқўпјҢжңүдёҖж¬ЎдёҚзҹҘйҒ“иҰҒеҺ»е“ӘиЈЎпјҢзҝ»й–ӢиЎҢжқҺз®ұзңӢеҲ°зүҮеӯҗйӮ„еңЁпјҢе°ұж”ҫйҖІDVD PlayerзңӢдәҶдёҖдёӢгҖӮгҖҠжқұгҖӢе’ҢгҖҠйҮ‘еҹҺе°ҸеӯҗгҖӢзҡ„и§’еәҰдёҚдёҖжЁЈпјҢгҖҠжқұгҖӢжҜ”ијғжҰӮеҝөгҖҒе“Іеӯёе‘ійҒ“пјҢдҪҶжҲ‘жҳҜеҫһз”ҹжҙ»йқўиө°пјҢе°ҚжҲ‘дҫҶиӘӘпјҢд№ҹиЁұеҫһз”ҹжҙ»йқўеҮәзҷјзҡ„жҺҘеҸ—еәҰжңғеҘҪдёҖй»һгҖӮ

еҒҮиӢҘ當еҲқеҠүе°Ҹжқұжүҫзҡ„дёҚжҳҜиіҲжЁҹжҹҜе’ҢжӮЁдҫҶеҹ·иЎҢгҖҠжқұгҖӢе’ҢгҖҠйҮ‘еҹҺе°ҸеӯҗгҖӢйҖҷе…©йғЁзҙҖйҢ„зүҮпјҢеҲҶеҲҘиЁҳйҢ„дёӢд»–еүөдҪңгҖҢжә«еәҠгҖҚгҖҒгҖҢйҮ‘еҹҺе°ҸеӯҗгҖҚзі»еҲ—дҪңе“Ғзҡ„йҒҺзЁӢпјҢйҖҷе…©йғЁзүҮеӯҗеҫҲеҸҜиғҪе°ұзҙ”зІ№жҳҜд»–еүөдҪңжӯ·зЁӢзҡ„еҒҙжӢҚпјҢдҪҶеӣ зӮәе…©дҪҚзҚЁзү№зҡ„иҰ–и§’иҲҮжӢҚж”қжүӢжі•пјҢе°Үе®ғжҸҗеҚҮеҲ°дёҖеҖӢй«ҳеәҰпјҢдҪҝеҫ—йҖҷе…©йғЁзҙҖйҢ„зүҮжңүдәҶзҚЁз«Ӣзҡ„з”ҹе‘ҪгҖӮ
е§ҡпјҡе…¶еҜҰжҲ‘еҖ‘еңЁдёҠжө·иҒҠеҲ°йҖҷеҖӢжӢҚж”қиЁҲз•«жҷӮд№ҹжҳҜйҖҷеҖӢжҰӮеҝөпјҢжҲ‘еҖ‘жӢҚж”қе…¶еҜҰжҳҜзӮәдәҶй…ҚеҗҲеҠүе°ҸжқұеңЁе°ӨеҖ«ж–Ҝ當代и—қиЎ“дёӯеҝғзҡ„з•«еұ•пјҢе°ӨеҖ«ж–ҜеҫҲеӨ§пјҢзңӢеұ•зҡ„еӢ•з·ҡжҳҜдёҖйҖІеҺ»е…ҲзңӢд»–зҡ„еүөдҪңж—ҘиЁҳгҖҒдёӯж®өзңӢд»–зҡ„з•«дҪңгҖҒжңҖеҫҢйҖІе…ҘдёҖеҖӢеұ•й–“зңӢзҙҖйҢ„зүҮпјҢйҖҡйҖҡйҡёеұ¬дёҖеҖӢй …зӣ®гҖӮе°ҚжҲ‘еҖ‘дҫҶи¬ӣпјҢеҰӮжһңйғҪиҠұжҷӮй–“еҺ»еҒҡпјҢдёҚжңғеҸӘжҳҜеҒҡдәҶж”ҫеңЁйӮЈеҖӢй …зӣ®иЈЎй ӯпјҢжүҖд»ҘиЎҚз”ҹеҮәдёҖеҖӢе®Ңж•ҙзүҲгҖӮ
гҖҠйҮ‘еҹҺе°ҸеӯҗгҖӢе°Қж–јеҠүе°Ҹжқұзҡ„еҲ»еҠғдё»иҰҒжҺЎеҸ–еҒҙжӢҚпјҢеҸҰиј”д»ҘдёҖдәӣе°ҚйҮ‘еҹҺ當ең°ең°жҷҜзҡ„жҸҸз№Ә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йҒёж“ҮйҖҸйҒҺиЁӘи«Үзҡ„ж–№ејҸиҲҮиў«ж”қиҖ…еұ•й–Ӣе°Қи©ұгҖӮж•ҙеҖӢжӢҚж”қжңҹй–“еӨ§з•ҘеҒҡйҒҺе№ҫж¬Ўи·ҹеҠүе°Ҹжқұжң¬дәәзҡ„иЁӘи«Үпјҹ
е§ҡпјҡе°ұзүҮеӯҗе‘ҲзҸҫзҡ„е…§е®№дҫҶиӘӘпјҢе°ұдёҖж¬ЎгҖӮеңЁйӮЈж¬Ўд№ӢеүҚпјҢжҲ‘д№ҹеҒҡйҒҺдёүж¬ЎпјҢдҪҶжҳҜжІ’з”ЁдёҠпјҢдёҖж¬ЎжҳҜд»–еҖ‘зҡ„е…„ејҹгҖҒзҲёзҲёдёҖж¬ЎгҖҒзҲёзҲёе’ҢеӘҪеӘҪдёҖж¬ЎгҖӮдҪҶжҲ‘д№ҹдёҚжҳҜз”ЁжҺЎиЁӘзҡ„ж–№ејҸпјҢиҖҢжҳҜзөҰдёҖеҖӢжғ…еўғеҫҢпјҢи®“д»–еҖ‘иҒҠдәӢжғ…гҖӮиӯ¬еҰӮз§ӢеӨ©жҷӮжңүз§Ӣиҹ№пјҢд»–еҖ‘еңЁиҳҶи‘Ұи•©иЈЎй ӯжңғйӨҠиһғиҹ№пјҢжңүдёҖе ҙжҳҜеҠүе°ҸжқұеҫһеүҚдёҖиө·з·ҙжӯҰиЎ“зҡ„дёүеҖӢе…„ејҹвҖ”вҖ”еҠӣдә”гҖҒжҲҗеӯҗгҖҒж—ӯеӯҗпјҢдёүеҖӢдәәйӮҠеҗғиһғиҹ№йӮҠиҒҠд»ҘеүҚеңЁжӯҰиЎ“йҡҠзҡ„дәӢжғ…гҖӮеҠүе°Ҹжқұ當е№ҙеңЁйҒёж“ҮиҰҒе°Ҳж”»жӯҰиЎ“йӮ„жҳҜзҫҺиЎ“пјҢеҫҢдҫҶйҒёдәҶзҫҺиЎ“гҖӮ

йӮЈдёҖж¬ЎиЁӘе•ҸдҫҜе°Һд№ҹеңЁпјҢеңЁд»–зңӢдҫҶпјҢжӢҚзүҮжҷӮж…ӢеәҰжңҖжҳҜйҮҚиҰҒпјҢйқўе°Қиў«ж”қиҖ…пјҢжҮү當иҰҒеұ•зҸҫе°ҠйҮҚпјҢи®“е°Қж–№иҷ•ж–јжңҖж”ҫй¬Ҷзҡ„зӢҖж…ӢдёӢгҖӮйҖҷдёҖж¬Ўзҡ„иЁӘе•Ҹд№ҹжҳҜеҹәж–јйҖҷжЁЈзҡ„жә–еүҮиҖҢзӯ–еҠғзҡ„пјҢиғҪеҗҰзЁҚеҫ®жҸҸиҝ°дёҖдёӢ當жҷӮзҡ„зӢҖж…Ӣпјҹ
е§ҡпјҡе…¶еҜҰжҲ‘еҖ‘йӮЈдёҖж¬Ўд№ҹдёҚз®—иЁӘе•ҸпјҢз®—жҳҜй–’иҒҠгҖӮйҖҷе°ҚзҙҖйҢ„зүҮдҫҶиӘӘжҳҜеҝ…иҰҒзҡ„пјҢеҰӮжһңйҖЈйҖҷеҖӢиЁӘе•ҸйғҪжІ’жңүпјҢеҸҜд»ҘжӢҝеҲ°зҡ„з·ҡзҙўе°ұжӣҙе°‘дәҶгҖӮйӮЈжҷӮеҖҷпјҢжҲ‘жӢҚпјҢдҫҜе°ҺгҖҒжңұеӨ©ж–Үд№ҹеңЁгҖӮжҲ‘еҖ‘еҺ»жүҫдәҶдёҖеҖӢзӮ•пјҢзҮ’еҫ—зҶұзҶұзҡ„пјҢеқҗеңЁзӮ•дёҠиҒҠеӨ©пјҢдёҖи·ҜиҒҠдёҖи·ҜиҒҠпјҢеҫҲж”ҫй¬ҶпјҢйӣ–然ж”қеҪұж©ҹеңЁпјҢдҪҶдәӢе…Ҳ已經иӘӘеҘҪе°ұжҳҜиҒҠпјҢд№ҹдёҚзӮәдәҶиҰҒиӘӘеҮәд»ҖйәјгҖӮдёҚйҒҺиҒҠдәҶе…©еҖӢе°ҸжҷӮпјҢеҶҚеҫһдёӯжүҫеҮәе…§е®№гҖӮ
жӮЁйҒҺеҺ»д№ҹжңүйҒҺжӢҚж”қзҙҖйҢ„зүҮзҡ„經驗пјҢжҳҜеҗҰд№ҹжҜ”ијғдёҚеӮҫеҗ‘жҺЎеҸ–иЁӘе•Ҹзҡ„еҪўејҸпјҹ
е§ҡпјҡжҜ”ијғе®Ңж•ҙзҡ„зҙҖйҢ„зүҮжҳҜгҖҠжҲ‘еҖ‘дёүеҖӢгҖӢпјҢеұ¬еӢһе·ҘеұҖ委託жӢҚж”қзҡ„еҪұзүҮгҖӮгҖҠжҲ‘еҖ‘дёүеҖӢгҖӢжңүиЁӘе•ҸпјҢдҪҶжҳҜжҲ‘зҡ„зүҮеӯҗеҹәжң¬дёҠиЁӘе•Ҹзҡ„йғҪеҫҲе°‘пјҢеӣ зӮәжҲ‘дёҚжңғиЁӘе•ҸгҖӮжҲ‘еҫҲдёҚж„ӣиӘӘи©ұпјҢжңүжҷӮеҖҷжІ’иҫҰжі•иҰҒжәқйҖҡпјҢжүҖд»Ҙжјёжјёи©ұжҜ”ијғеӨҡпјҢдҪҶи©ұйӮ„жҳҜдёҚжҳҜеҫҲжә–гҖӮиЁӘе•ҸйҖҷ件дәӢе°ҚжҲ‘жҳҜеҖӢиІ ж“”пјҢе°ұеғҸгҖҠжҲ‘еҖ‘дёүеҖӢгҖӢпјҢжҲ‘еҲ—дәҶе•ҸйЎҢеҮәдҫҶд№ӢеҫҢпјҢжҳҜи«Ӣе·Ҙж®ӨеҚ”жңғзҡ„дәә幫жҲ‘иЁӘе•ҸпјҢз”Ёд»–зҡ„з«Ӣе ҙдҫҶиЁӘе•ҸпјҢд»–еҫҲе®№жҳ“еҫһжҲ‘зҡ„е•ҸйЎҢеҶҚ延伸гҖӮеҖӢжҖ§дҪҝ然пјҢжҲ‘еҫҲе®№жҳ“е•ҸеҖӢе…©йЎҢе°ұе•ҸдёҚдёӢеҺ»дәҶгҖӮ
е°Һжј”йҒҺеҺ»д№ҹз•«з•«пјҢйҖҷж¬Ўжңүж©ҹжңғи·ҹжӢҚдёҖдҪҚ畫家пјҢиҝ‘иә«ж—Ғи§Җе…¶еүөдҪңйҒҺзЁӢпјҢеҫһдёҖеҖӢеүөдҪңиҖ…зҡ„и§’еәҰзңӢеҸҰдёҖдҪҚеүөдҪңиҖ…гҖӮжӮЁиҰәеҫ—еңЁйҖҷж¬Ўзҡ„жӢҚж”қ經驗дёӯ收зҚІжңҖеӨ§зҡ„жҳҜд»Җйәјпјҹ
е§ҡпјҡжҲ‘еңЁйҖҷеҖӢиЎҢжҘӯеҫҲд№…дәҶпјҢдёҖи·ҜдёӢдҫҶд№ҹдәҢеҚҒе№ҙдәҶгҖӮеңЁиҮӘе·ұзҡ„иЎҢжҘӯдәҢеҚҒе№ҙжңғжңүдёҖзЁ®зӣІй»һпјҢйҖҷдёҖж¬Ўи—үз”ұеҠүе°ҸжқұзҙҖйҢ„зүҮзҡ„жӢҚж”қе·ҘдҪңпјҢи®“жҲ‘еңЁиҮӘе·ұзҡ„зӣІй»һиЈЎй ӯжү“й–ӢдәҶдёҖдәӣгҖӮе…¶еҜҰи—қиЎ“еңЁзІҫзҘһдёҠжҳҜдёҖжЁЈзҡ„пјҢеҠүе°Ҹжқұз®—жҳҜдёӯеңӢ當代еҫҲйҮҚиҰҒзҡ„дёҖеҖӢ畫家пјҢдҪ жңғзңӢеҲ°д»–еҒҡдәӢзҡ„ж–№жі•гҖҒд»–зҡ„жңҹеҫ…е’Ңж“”жҶӮпјҢдҪ жңғзҷјзҸҫпјҢеҺҹдҫҶи·ҹиҮӘе·ұиЎҢжҘӯиЈЎй ӯи©ІиҮӘз”ұжҲ–иҖ…и©ІдёҚиҮӘз”ұзҡ„йӮЈеҖӢжқұиҘҝжҳҜдёҖжЁЈзҡ„гҖӮ

жӮЁжӣҫжҸҗйҒҺпјҡгҖҢзҙҖйҢ„зүҮжӢҚж”қзҡ„жҳҜз”ҹжҙ»зҡ„еҺҹеһӢгҖҚпјҢиғҪеҗҰи«ӢжӮЁеӨҡиҒҠдёҖиҒҠпјҹ
е§ҡпјҡзҙҖйҢ„зүҮе°ұжҳҜз”ҹжҙ»зҡ„еҺҹеһӢгҖӮжӢҚйӣ»еҪұпјҢе°Өе…¶жҲ‘и·ҹдҫҜе°ҺеңЁжӢҚпјҢе…¶еҜҰйғҪжғіиҰҒеүөеҮәз”ҹжҙ»зҡ„еҺҹеһӢпјҢе°ұз®—жӢҚеҠҮжғ…зүҮгҖӮ當然еҫ—еҺ»иӘҝеәҰзҡ„жқұиҘҝдёҚдёҖжЁЈгҖӮзҙҖйҢ„зүҮпјҢе°ҚжҲ‘дҫҶи¬ӣжҳҜжңҖдёӯеҝғзҡ„пјҢжӢҚж”қзҡ„е°ұжҳҜз”ҹжҙ»зҡ„еҺҹиІҢпјҢйӮЈеҖӢжқұиҘҝжҳҜдҪ дёҚиғҪжӣҙеӢ•зҡ„пјҢйҖҷжҳҜдёҖеҖӢжўқ件гҖҒдёҖеҖӢеҺҹеүҮгҖӮдҪ иғҪеӨ еҺ»жӢҚеҲ°з”ҹжҙ»зҡ„еҺҹеһӢпјҢеҶҚжҠҠе®ғзө„еҗҲеҮәдҫҶпјҢжҲ–жҳҜжҲ‘еҺ»зңӢеҲҘдәәеҰӮдҪ•жӢҚдәә家з”ҹжҙ»зҡ„еҺҹеһӢпјҢе°ҚжӢҚйӣ»еҪұзҡ„дәәе…¶еҜҰжҳҜеҫҲйҮҚиҰҒзҡ„пјҢйҖҷйғЁд»Ҫд№ҹжҳҜеҫҲеҘҪзңӢзҡ„гҖӮеӣ зӮә既然иҰҒжӢҚпјҢиЎЁзӨәе®ғзө•е°ҚжҳҜеҖӢиӯ°йЎҢпјҢжҲ–жҳҜж„ҹиҰәиҰҒж”ҫеӨ§зҡ„жқұиҘҝпјҢеҺ»зңӢеҲ°з”ҹжҙ»зҡ„еҺҹеһӢе°ҚеҒҡйӣ»еҪұзҡ„дәәдҫҶи¬ӣжҳҜжңҖеҘҪзҡ„гҖӮ
е°ҚжҲ‘дҫҶи¬ӣпјҢеҰӮжһңжңүдәәиҰҒе№№йӣ»еҪұе…¶еҜҰжҮүи©ІеҫһжӢҚзҙҖйҢ„зүҮй–Ӣе§ӢпјҢдёҚз®ЎдҪ з”Ёзҡ„жҳҜд»ҖйәјйЎҢзӣ®пјҢжӢҚеҲ°зҡ„е°ұжҳҜз”ҹжҙ»зҡ„еҺҹеһӢгҖӮжҺҘи§ёеҫ—ж„Ҳд№…пјҢдҪ зҡ„жҠҪеұңе Ҷеҫ—жқұиҘҝж„ҲеӨҡпјҢе°ҮдҫҶеңЁиҷ•зҗҶеҠҮжғ…зүҮзҡ„жҷӮеҖҷдҪ зҡ„жӢӣжӣҙеӨҡгҖӮйӣ»еҪұйӮ„жҳҜеҫ—з”Ёз”ҹжҙ»зҡ„жқұиҘҝеҺ»зҙҜз©ҚпјҢзёұдҪҝе•ҶжҘӯзүҮд№ҹдёҖжЁЈпјҢдҪ йңҖиҰҒйҖҷдәӣеә•еӯҗпјҢеңЁжӢҚж”қзҙҖйҢ„зүҮзҡ„жҷӮеҖҷе…¶еҜҰжҳҜеҸҜд»ҘзҚІеҫ—еҫҲеӨҡзҡ„гҖӮдҪҶжҳҜжӢҚзҙҖйҢ„зүҮеҫҲзҙҜпјҢеӣ зӮәжӢҚе®ҢдҪ йғҪдёҚзҹҘйҒ“жӢҚеҲ°жІ’жңүпјҢеЈ“еҠӣеӨ§зҡ„жҷӮеҖҷдҪ жңғиҰәеҫ—жӢҚзҡ„жҳҜдёҖе ҶеһғеңҫпјҢеҫ—еңЁиЈЎй ӯеҺ»жүҫгҖӮ
ж—ҘеүҚеҠүе°ҸжқұеңЁеә§и«ҮжңғдёҠжҸҗеҲ°пјҢжӮЁжӣҫи·ҹд»–иӘӘпјҡгҖҢжҲ‘дёҖе®ҡиәІй–Ӣиў«жӢҚж”қиҖ…зҡ„еҝ…經д№Ӣи·ҜгҖӮгҖҚеҸҰеӨ–пјҢд»–д№ҹиӘӘпјҢжӮЁжӢҚзҡ„йҮ‘еҹҺжҜ”д»–жғіеғҸдёӯдҫҶеҫ—еӨ§пјҢжңүдәӣе ҙжҷҜеңЁд»–ж„Ҹж–ҷд№ӢеӨ–гҖӮи«ӢжӮЁи«Үи«ҮйҖҷдёҖй»һпјҢд»ҘеҸҠйҖҷеӣһеңЁйҮ‘еҹҺ當ең°зҡ„жҷғйҒҠиҲҮжӢҚж”қ經驗гҖӮ
е§ҡпјҡйҖҷдёҖе®ҡзҡ„пјҢжҲ‘зңӢжҷҜйғҪеңЁзңӢйҖҷеҖӢпјҢжҲ‘дёҚжңғиІҝ然ең°дёҖдёӢе°ұжҠҠж©ҹеҷЁжӢҝеҮәдҫҶпјҢжҲ‘еҖ‘дёҖе®ҡжңғйҖІеҺ»иЈЎйқўж··пјҢдҪ жңғж··еҮәдёҖеҖӢеӢ•з·ҡдҫҶпјҢдәә家зҡ„еӢ•з·ҡпјҢдёҚжҳҜдҪ зҡ„еӢ•з·ҡгҖӮжҲ‘дёҖе®ҡиҰҒйҒҝй–ӢйҖҷдәӣеӢ•з·ҡпјҢиӯ¬еҰӮзҸҫеңЁж”қеҪұж©ҹиҷ•еңЁдёҖеҖӢд»–еӢ•з·ҡиЈЎй ӯеҝ…經д№Ӣи·ҜпјҢйӮЈд»–ж°ёйҒ йҒҝдёҚжҺүжҲ‘е•ҠпјҢж”қеҪұж©ҹж°ёйҒ еңЁд»–йқўеүҚгҖӮж”қеҪұж©ҹе…¶еҜҰиҰҒиҷ•зҡ„зҜ„еңҚжҳҜеңЁд»–еӢ•з·ҡд№ӢеӨ–пјҢиәІеңЁйӮЈйӮҠпјҢзӣЎйҮҸдёҚе№Іж“ҫд»–гҖӮжҲ‘дёҖе®ҡиҷ•еңЁжңҖеӨ–еңҚпјҢжҲ–иҖ…жҳҜж №жң¬дёҚжңғеҪұйҹҝдәә家еӢ•з·ҡзҡ„ең°ж–№пјҢзёұдҪҝжңүдёҖеҖӢеҫҲжјӮдә®зҡ„дҪҚзҪ®пјҢдҪҶжңғеҪұйҹҝдәә家зҡ„еӢ•з·ҡпјҢжҲ‘еҜ§йЎҳдёҚиҰҒгҖӮ
жҲ‘е№ҫд№ҺйғҪеңЁиө°пјҢжҲ‘иө°йҒҺзҡ„ең°ж–№жҜ”д»–еҖ‘еӨҡгҖӮжҲ‘жңүеҖӢең°йҷӘпјҢе°ұжҳҜеҪұзүҮдёӯиә«дёҠжңүеҲәйқ’зҡ„ж—ӯеӯҗпјҢжҲ‘иҰҒд»–её¶жҲ‘еҺ»иө°зҡ„ең°ж–№жҜ”д»–иө°йҒҺзҡ„ең°ж–№йӮ„еӨҡгҖӮжҲ‘е°ұжҳҜдёҚзҹҘйҒ“иҰҒеҺ»е“ӘиЈЎжүҚдёҖзӣҙиө°пјҢд»–еҖ‘жҳҜзҹҘйҒ“иҰҒеҺ»е“ӘиЈЎжүҖд»ҘдёҚз”ЁдёҖзӣҙиө°гҖӮиӯ¬еҰӮжҲ‘е•Ҹд»–е“ӘиЈЎзҫҺпјҢд»–е°ұиӘӘпјҡгҖҢйӮЈиЈЎзҫҺпјҢжҲ‘её¶дҪ еҺ»зңӢзңӢгҖӮгҖҚеҸҜйӮЈжҳҜд»–зҗҶи§Јзҡ„зҫҺпјҢдёҚжҳҜжҲ‘зҗҶи§Јзҡ„зҫҺпјӣжҲ–жҳҜд»–иӘҚзҹҘдёӯжҲ‘зҡ„ж„ҸжҖқжҳҜиҰҒйҖҷеҖӢпјҢе…¶еҜҰдёҚжҳҜгҖӮжңүжҷӮеҖҷеҲ°дәҶжҹҗиҷ•пјҢзҹҘйҒ“еҺҹдҫҶд»–жҳҜиҰҒеё¶жҲ‘дҫҶзңӢйҖҷеҖӢпјҢжҲ‘еҸҲиӘӘпјҢйӮЈжҲ‘еҖ‘еҶҚеҲ°йӮЈе…’зңӢзңӢпјҢе°ұдёҖзӣҙиө°гҖӮ
зүҮй ӯжңүгҖҢйҮ‘еҹҺгҖҚе…©еҖӢеӯ—пјҢжІ’жңүдәәзҹҘйҒ“еңЁе“ӘиЈЎгҖӮйҮ‘еҹҺйӮЈйәје°ҸпјҢдҪҶзңӢйҒҺзүҮеӯҗзҡ„жІ’жңүдәәзҹҘйҒ“еңЁе“ӘиЈЎпјҢдҪ зӣёдёҚзӣёдҝЎпјҹжҲ‘иҰәеҫ—е°ұжҳҜд№…дәҶпјҢд№…дәҶдҪ е°ұзңӢдёҚеҲ°дәҶпјҢйӮЈе…©еҖӢеӯ—е°ұеңЁдёҖеҖӢз ҙе…¬ең’зҡ„й–ҖеҸЈпјҢе®ғеҜ«гҖҢзҫҺеҢ–йҮ‘еҹҺгҖҚпјҢдёҚйҒҺжҲ‘еҸӘз”ЁдәҶгҖҢйҮ‘еҹҺгҖҚе…©еҖӢеӯ—гҖӮ
еҹҺй„үе·®и·қж„ҲжӢүж„Ҳиҝ‘е…¶еҜҰдёҚеҘҪпјҢеӣ зӮәж„ҲдҫҶж„ҲжІ’жңүеә•еӯҗгҖӮеҢ…жӢ¬еғҸе°ҸжқұйҖҷзЁ®и—қ術家пјҢд»–зҡ„йӨҠжҲҗе…¶еҜҰжҳҜеңЁйҮ‘еҹҺпјҢеңЁй„үдёӢпјҢдёҚжҳҜеңЁеҢ—дә¬гҖӮйҖҷж¬ЎйҮ‘йҰ¬еҪұеұ•жҲ‘зңӢдәҶж—Ҙжң¬еӢ•з•«е°Һжј”ж–°жө·иӘ зҡ„дҪңе“ҒпјҢд»–иў«иӯҪзӮәе®®еҙҺй§ҝзҡ„жҺҘзҸӯдәәпјҢд№ҹиў«иӯҪзӮәгҖҢиғҢжҷҜзҘһгҖҚпјҢжҲ‘еҺ»иҒҪд»–зҡ„и¬ӣеә§пјҢд»–д№ҹжҳҜе°ҸжҷӮеҖҷдҪҸеңЁй„үдёӢпјҢжүҖжңүйқҲж„ҹдҫҶжәҗйғҪеңЁй„үдёӢпјҢеҢ…жӢ¬е…үз·ҡгҖҒжІіжөҒгҖҒеұұгҖҒз©әж°ЈзӯүгҖӮжүҖд»ҘжҲ‘еҺ»йҮ‘еҹҺеҫҲе®№жҳ“жңғжңүдёҖеҖӢе°ҚжҜ”и·‘еҮәдҫҶпјҢеҫҲеӨҡжқұиҘҝдҪ 當然зҹҘйҒ“пјҢдҪҶжҳҜж–°й®®пјҢеӣ зӮәеҸ°зҒЈе·Із¶“дёҚеҶҚжңүдәҶгҖӮйӮЈйӮҠзҡ„йҮ‘еҹҺйҖ зҙҷе» и·ҹеҸ°зҒЈзҡ„зі–е» жҳҜдёҖжЁЎдёҖжЁЈзҡ„пјҢжҲ‘еүӣеҮәйҒ“當еҠ©зҗҶиҰҒеҺ»еӢҳжҷҜзҡ„жҷӮеҖҷпјҢеёёеҺ»зі–е» еӢҳжҷҜпјҢеҒ¶зҲҫйӮ„жңғйҒҮеҲ°йҒӢз”ҳи”—зҡ„зҒ«и»ҠгҖҒе» д№ҹйӮ„еңЁгҖҒе®ҝиҲҚйӮ„жңүдҪҸдәәпјҢзҸҫеңЁйғҪеҸӘеү©и§Җе…үдәҶгҖӮдҪҶжҳҜдҪ еҲ°йҮ‘еҹҺпјҢжңғзҷјзҸҫйғҪжңүпјҢиҖҢдё”йғҪдёҖжЁЈгҖҒйғҪйӮ„еңЁпјҢе°ұжңғжҠҠд»ҘеүҚеҺ»зңӢзі–е» зҡ„ж„ҹиҰәжӢүеӣһдҫҶгҖӮжүҖд»ҘжҲ‘йқһеҫ—иҰҒжӢҚеҲ°д»–еҖ‘дёҠе·ҘпјҢеҺ»е“ӘиЈЎе·ҘдҪңпјҢеӣһ家жҖҺйәјеӣһгҖӮжҲ‘еҫҲе–ңжӯЎд»–еҖ‘еӣһзЁӢдёӢи»ҠжҷӮзӣҙжҺҘи·іи»Ҡзҡ„з•«йқўпјҢе…үзӮәдәҶйҖҷеҖӢжҲ‘и·‘дәҶеҝ«еҚҒж¬ЎпјҢжҲ‘е°ұжҳҜдёҖе®ҡиҰҒжӢҚд»–еҖ‘дёӢи»ҠйӮЈеҖӢж„ҹиҰәгҖӮйҖҷеҖӢж„ҹиҰәе“ӘдҫҶзҡ„пјҹе°ұжҳҜд»ҘеүҚе°ҚеҸ°зҒЈзҡ„ж„ҹиҰәгҖӮ

еҘҪеғҸе°ұйҖЈйҮ‘еҹҺдәәзңӢдәҶйҖҷйғЁзүҮйғҪиҰәеҫ—зҫҺеҫ—йҒҺзҒ«пјҢдёҚеғҸйҮ‘еҹҺпјҹ
е§ҡпјҡжҲ‘и©Ұең–жӢҚеҠүе°Ҹжқұеҝғдёӯзҡ„йҮ‘еҹҺпјҢжҲ‘зңӢйҒҺдёҖдәӣд»–зҡ„иҖҒз…§зүҮпјҢз•ҷдёӢзҡ„иЁҳжҶ¶еҹәжң¬дёҠжҳҜзҫҺеҘҪзҡ„гҖӮе…¶еҜҰжҲ‘иҰәеҫ—йӮЈдәӣжүҖи¬Ӯзҡ„зҫҺжҳҜзө„еҗҲйҒҺзҡ„жғ…з·’и®“д»–еҖ‘иҰәеҫ—зҫҺ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жҹҗдёҖеҖӢе ҙжҷҜеҫҲзҫҺгҖӮйӮ„жҳҜжҲ‘зҗҶи§ЈйҢҜиӘӨпјҹеҪұеғҸжІ’жңүиў«зө„еҗҲгҖҒиў«йҷ„еҠ ж„Ҹзҫ©зҡ„жҷӮеҖҷе“ӘжңүзҫҺпјҹзңӢжҜӣзүҮзҡ„жҷӮеҖҷеҫҲжҺҷжүҺеҘҪдёҚеҘҪгҖӮе”ҜдёҖжҲ‘иҰәеҫ—зҫҺзҡ„е°ұжҳҜйӮЈзүҮиҳҶи‘Ұи•©гҖӮ
йҖҷйғЁзүҮзҡ„ж”қеҪұеҫҲзҫҺпјҢд№ҹе…ҘеңҚдәҶйҮ‘йҰ¬зҚҺжңҖдҪіж”қеҪұгҖӮжң¬зүҮеҗҢжҷӮжҺЎз”ЁHDе’Ң16йҮҗзұійӣҷж©ҹжӢҚж”қпјҢйӮЈеҸ°16йҮҗзұіж”қеҪұж©ҹжӢҚеҮәдҫҶзҡ„з•«йқўе°Өе…¶еҲҘе…·е‘ійҒ“гҖӮ
е§ҡпјҡжҲ‘й•·жңҹжңүеңЁз”ЁдёҖеҸ°Bolex 16йҮҗзұіж”қеҪұж©ҹпјҢйҖҷжҳҜз‘һеЈ«еңЁдәҢжҲ°жҷӮеҖҷеҒҡзҡ„ж©ҹеҷЁпјҢз©әжҠ•зөҰиЁҳиҖ…з”Ёзҡ„пјҢжүҖд»ҘиҰҒеҫҲж–№дҫҝпјҢдёҚиғҪжңүйӣ»пјҢе®ғжҳҜдёҠзҷјжўқзҡ„пјҢдёҖж¬ЎжӢҚе°ұжҳҜдәҢеҚҒе№ҫз§’гҖӮйҖҷеӣһе°ұеё¶йҖҷеҖӢеҺ»жӢҚгҖӮе…¶еҜҰжҲ‘еҖ‘й•·жңҹйғҪжңүйҖҷжЁЈеңЁз”ЁпјҢгҖҠ10+10гҖӢдёӯпјҢдҫҜе°Һзҡ„гҖҠй»ғйҮ‘д№ӢејҰгҖӢйӮЈж®өж”қеҪұжҳҜжҲ‘пјҢд№ҹжҳҜдёҖеҚҠ35йҮҗзұіпјҢдёҖеҚҠз”ЁжҲ‘йӮЈеҸ°е°Ҹ16йҮҗзұіжӢҚгҖӮеңЁе»Је‘ҠиЈЎйқўд№ҹз”ЁеҫҲеӨҡгҖӮйҖҷеҸ°ж”қеҪұж©ҹзҡ„еҘҪиҷ•жҳҜе®ғзҡ„ж®әеӮ·еҠӣеҫҲдҪҺпјҢйҷӨдәҶжңүеҷӘйҹід№ӢеӨ–пјҢеёёеёёжңғи®“дәә家иҰәеҫ—жӢҝйӮЈеҖӢжӢҚжІ’д»ҖйәјпјҢдёҚеғҸHDж”қеҪұж©ҹдәә家дёҖзңӢе°ұиӘҚе®ҡжҳҜй«ҳ科жҠҖпјҢжӢҚйӣ»еҪұзҡ„пјҢе°Өе…¶жҳҜеңЁйҮ‘еҹҺйӮЈзЁ®е°Ҹең°ж–№пјҢеҫҲе®№жҳ“иў«еҜҹиҰәгҖӮиӯ¬еҰӮжҲ‘еҺ»иЎ—жӢҚпјҢжӢҚеёӮе ҙпјҢжҲ‘еңЁеүҚйқўжӢҚпјҢжҲ‘зҡ„иЈҪзүҮиҰҒиә«е…јйҢ„йҹіпјҢдҪҶд»–дёҚиғҪеңЁжҲ‘ж—ҒйӮҠпјҢиҰҒйӣўжҲ‘еҚҒзұійҒ пјҢжҲ‘еҰӮжһңжңүжӢҚпјҢжңғжңүдёҖеҖӢеӢ•дҪңпјҢд»–йҒ йҒ зңӢпјҢзӯүжҲ‘жҸӣдёӢдёҖеҖӢй»һдәҶпјҢд»–жүҚеҺ»еҺҹдҫҶйӮЈеҖӢй»һжҠҠиҒІйҹіж”¶иө·дҫҶпјҢеӣһй ӯжҲ‘еҖ‘еңЁеүӘжҺҘе®Өе°ҚеҗҢжӯҘпјҢжҠҠиҒІйҹіе°Қеҫ—еҘҪеғҸжҳҜеҗҢжӯҘгҖӮжңүдёҖдәӣе ҙжҷҜжҲ‘жңғе…©еҖӢйғҪжӢҚпјҢHDйӮЈдёҖеҸ°жҳҜжҺӣзЎ¬зўҹпјҢдёҖй–Ӣж©ҹеҸҜд»Ҙй–Ӣе…©еҖӢеӨҡе°ҸжҷӮпјҢжҲ‘еёёй–Ӣж©ҹдәҶд»ҘеҫҢжӢҝйӮЈеҸ°16йҮҗзұіеңЁж—ҒйӮҠжӢҚгҖӮ
еҺҹе…Ҳе…¶еҜҰжҳҜзӮәдәҶж–№дҫҝпјҢдҪҶеҫҢдҫҶзө„еҗҲеҮәдҫҶжңүдёҖзЁ®е‘ійҒ“пјҢжңүй»һеғҸдё»гҖҒе®ўи§Җзҡ„и·іеӢ•гҖӮеғҸе°Ҹжқұд№ҹжҳҜеҫҲз–‘жғ‘пјҢе•ҸжҲ‘16йҮҗзұіе’ҢHDзҡ„з•«йқўжҖҺйәјзө„еҗҲпјҢжҲ‘иӘӘжҲ‘д№ҹдёҚзҹҘйҒ“пјҢеҸӘжҳҜжғіиӘӘжҮүи©ІеҸҜд»Ҙзө„еҗҲгҖӮ當еҲқжӢҚе®ҢеӣһеҲ°еҸ°зҒЈеҫҢпјҢиҰҒдәӨеҮәзҡ„第дёҖеҖӢзүҲжң¬еҫҲ趕пјҢеҸӘжңүдәҢеҚҒе№ҫеҖӢе·ҘдҪңеӨ©гҖӮжүҚеүӣеӣһдҫҶпјҢж„ҹиҰәйӮ„жІ’ж–·пјҢе°ұжҶ‘зӣҙиҰәдёҖзӣҙжӢјдёҖзӣҙжӢјпјҢеҶҚеӣһй ӯзңӢпјҢдҝ®дёҖдёӢдҝ®дёҖдёӢпјҢиҮӘ然иҖҢ然е°ұеҪўжҲҗдәҶгҖӮHDе’Ң16йҮҗзұідәӨдә’и·іеӢ•зҡ„жҷӮеҖҷе°ҚжҲ‘дҫҶи¬ӣжІ’жңүиІ ж“”пјҢжҲ‘е°ұи®Ҡеҫ—жӣҙеӨ§иҶҪдҪҝз”ЁгҖӮ
жҲ‘жң¬дҫҶжҮүи©ІжҳҜдәӨзөҰд»–дёҖеҖӢдәҢеҚҒеҲҶйҗҳе·ҰеҸізҡ„жқұиҘҝпјҢеҸҜжҳҜжҲ‘еүӘдёҚзҹӯпјҢжүҖд»ҘеҫҢдҫҶеңЁе°ӨеҖ«ж–Ҝж”ҫжҳ зҡ„зүҲжң¬еҝ«дёҖеҖӢе°ҸжҷӮгҖӮ

з”ЁйӮЈеҸ°16йҮҗзұіж”қеҪұж©ҹжӢҚж”қеҮәдҫҶзҡ„з•«йқўиіӘж„ҹпјҢеҫҲеӨҡжҷӮеҖҷе°ұеғҸдёҖе№…е№…жөҒеӢ•зҡ„з•«гҖӮеңЁжӢҚгҖҠйҮ‘еҹҺе°ҸеӯҗгҖӢзҡ„жҷӮеҖҷпјҢжңүдјҒең–и—үз”ұйҖҷйғЁзҙҖйҢ„зүҮи·ҹеҠүе°Ҹжқұзҡ„з№Әз•«еұ•й–ӢдёҖзЁ®д»ҖйәјжЁЈзҡ„е°Қи©ұй—ңдҝӮе—Һпјҹ
е§ҡпјҡжңүе•ҠпјҢжҲ‘еҺ»йӮЈйӮҠе”ҜдёҖзҡ„дјҒең–е°ұжҳҜд»–зҡ„з•«еӨ–иҮіе°‘иҰҒж„ҹиҰәйӮ„жҳҜз•«зҡ„дёҖйғЁд»ҪпјҢжҲ‘жІ’жҠҠжҸЎзҡ„е…¶еҜҰд№ҹе°ұжҳҜйҖҷеҖӢгҖӮеҰӮжһңйҖҷеҖӢжІ’еҒҡеҲ°пјҢд»–зҡ„з•«жңғеұ•еҮәпјҢжҲ‘зҡ„еҪұеғҸзӯүж–јжҳҜз•«дҪңзҡ„з«Ӣй«”йқўпјҢеҰӮжһңз•«еӨ–зҡ„з•«жІ’жңүйҖ жҲҗзҡ„и©ұпјҢиҮіе°‘жҲ‘жӢҚзҡ„йҖҷдәӣжқұиҘҝеҸҜд»ҘиЈңи¶ід»–зҡ„з•«зҡ„з«Ӣй«”йғЁд»ҪгҖӮ
еңЁеҪұзүҮдёӯпјҢеҠүе°ҸжқұжңүдёҖеӣһеңЁдҪңз•«жҷӮпјҢжҸҗеҲ°йӣ»еҪұе’Ңз№Әз•«зҡ„жӯ§з•°пјҢжҢҮеҮәз№Әз•«жң¬иә«зҡ„дҫ·йҷҗд№Ӣиҷ•гҖӮд»–иӘӘпјҡгҖҢз№Әз•«еңЁзҹӯжҷӮй–“е…§з•«дёҚеҮәдҫҶйӮЈйәјеӨҡзҡ„е…§е®№пјҢеҸӘиғҪйҒёж“ҮдёҖеҖӢи§’еәҰпјҢйӮЈйҖҷжҷӮеҖҷжӢҚйӣ»еҪұеҫҲеҗҲйҒ©пјҢе®ғе°ұзӯүж–је…Ёж–№дҪҚе°ұиғҪдәӨеҫ…гҖӮгҖҚжӮЁиҮӘе·ұжҖҺйәјзңӢпјҹ
е§ҡпјҡйӣЈеәҰдёҚдёҖжЁЈпјҢе–®е°ұе–®дёҖеҪұеғҸдҫҶи¬ӣпјҢз№Әз•«зўәеҜҰеӨӘйӣЈдәҶгҖӮе°ұеғҸжҲ‘иҮӘе·ұжҳҜж”қеҪұеё«пјҢжҲ‘иғҪжӢҚеӢ•ж…Ӣж”қеҪұпјҢи·ҹе№ійқўж”қеҪұжҜ”иө·дҫҶпјҢжҲ‘еҸҲиҰәеҫ—е№ійқўж”қеҪұжҜ”жҲ‘еҖ‘еҺІе®іеҫҲеӨҡпјҢеӣ зӮәд»–еҫ—з”ЁдёҖејөз…§зүҮе°ұи¬ӣжё…жҘҡпјҢи·ҹжҲ‘дҪҝз”ЁйҖЈзәҢз•«йқўдёҚдёҖжЁЈгҖӮ

еҠүе°Ҹжқұзҡ„з№Әз•«дҪңе“ҒеҫҲйҮҚиҰ–дәәе’Ңз©әй–“зҡ„й—ңдҝӮпјҢд»–жңғдәӢе…Ҳзү©иүІеҘҪеҗҲйҒ©зҡ„е ҙжҷҜпјҢе°ҮдәәзҪ®ж”ҫеңЁйӮЈеҖӢеҜҰй«”зҡ„з©әй–“иЈЎпјҢзҸҫе ҙдҪңз•«гҖӮе°Қж–јз©әй–“зҡ„йҒёж“ҮпјҢеҠүе°ҸжқұиҮӘжңүдёҖеҘ—жЁҷжә–пјҢд»–еңЁеҖӢдәәеүөдҪңж—ҘиЁҳдёӯе°ұеҜ«йҒ“пјҡгҖҢдёҠеҚҲеҺ»еҠӣдә”家пјҢеҫҲдәӮеҸҜз•«гҖӮжҲҗеӯҗ家еғҸиі“йӨЁпјҢе…ҲдёҚз•«гҖӮж—ӯеӯҗ家пјҢеҺҹз”ҹж…ӢпјҢеҸҜз•«гҖӮгҖҚеҸҰжңүдёҖеӣһпјҢд»–еҺ»дәҶе°ҸиұҶ家пјҢз•«е…·д№ҹжҠ¬еҺ»дәҶпјҢдҪҶиҰӢеҘ№е®¶иЈЎд№ҫд№ҫж·Ёж·ЁжІ’д»Җйәје…§е®№пјҢеҸҲжұәиӯ°жҮүи©ІжӢүеҺ»еӨ–й ӯз•«гҖӮ
е§ҡпјҡиҖҢдё”д»–и©•дј°зҡ„еҸҜиғҪйӮ„жҜ”жҲ‘еҖ‘жӣҙеӨҡпјҢиӯ¬еҰӮд»–иҰәеҫ—е°ҸиұҶ家畫иө·дҫҶжІ’ж„ҸжҖқпјҢеғҸиі“йӨЁпјҢеӣ зӮәеҫҲзҸҫд»ЈгҖҒеҫҲд№ҫж·ЁпјӣеҠӣдә”家е°ұжҳҜж»ҝж»ҝзҡ„пјҢе…©еӨ«еҰ»пјҢе–®е…ғз©әй–“д№ҹе°ҸпјҢжүҖжңүжқұиҘҝйғҪе ҶеңЁиЈЎйқўпјҢе°Өе…¶еҠӣдә”жҳҜжңүд»Җйәјзі§йЈҹе°ұж’ҝеӣһ家гҖӮе°ҸиұҶ家е°ұжҳҜд»ҖйәјйғҪжІ’жңүпјҢеҸҜиғҪдёҖејөжІҷзҷјеҫҢйқўе°ұжҳҜдёҖйқўеӨ§зҷҪзүҶпјҢжҖҺйәјж“әе°ұжҳҜйҖҷжЁЈпјҢжІ’еҫ—еҘҪз•«пјҢдҪҶжҳҜе°ұеҪұеғҸиҖҢиЁҖпјҢжҲ‘жңүеӨҡи§’еәҰеҸҜд»Ҙе‘ҲзҸҫпјҢеҰӮжһңеҘ№дёҚеҒҡйЈҜпјҢеңЁе®¶жҜҸеӨ©йғҪй–’й–’жІ’дәӢе№№пјҢжҲ‘е°ұжӢҚд»–еңЁе®¶й–’й–’жІ’дәӢе№№гҖӮзӮәд»Җйәјй–’й–’жІ’дәӢе№№пјҹеӣ зӮәйҖҷжЁЈйӮЈжЁЈпјҢжҲ‘еҸҜд»ҘеҺ»жӢҚйҒҺдҫҶпјҢиӯ¬еҰӮеҘ№е…Ҳз”ҹжҳҜе№№з”ҡйәјзҡ„пјҢдёҖе®ҡжңүз…§зүҮеңЁж«Ҙж«ғиЈЎй ӯеҸҜд»ҘдҪҝз”ЁпјҢеҢ…жӢ¬еҫһж«Ҙж«ғзҡ„ж“әиЁӯеҸҜд»ҘзҹҘйҒ“д»–жҳҜжҖҺжЁЈзҡ„дәәпјҢи§’еәҰе°ұжңғеҮәдҫҶгҖӮз№Әз•«е°ұжӢјж№ҠдёҚеҲ°йҖҷеҖӢдәәзҡ„е‘ійҒ“гҖӮ

е°ҚжӮЁиҖҢиЁҖпјҢжӢҚж”қгҖҠйҮ‘еҹҺе°ҸеӯҗгҖӢеҹәжң¬дёҠд№ҹжҳҜеңЁиҷ•зҗҶеҠүе°ҸжқұйҖҷеҖӢдәәи·ҹйҮ‘еҹҺйҖҷеҖӢз©әй–“зҡ„й—ңдҝӮпјҢжӮЁиҮӘе·ұжҳҜжҖҺйәјжҖқиҖғзҡ„пјҹеҪұзүҮдёӯеҘҪеғҸжІ’жҖҺйәјзңӢиҰӢеҠүе°ҸжқұеңЁйҮ‘еҹҺиЈЎйҒҠиө°зҡ„з•«йқўпјҹ
е§ҡпјҡжҲ‘иҰәеҫ—д№ҹиЁұеҸӘиҰҒжҠҠд»–зҡ„жңӢеҸӢжӢҚеҲ°пјҢзҲ¶жҜҚжӢҚеҲ°пјҢжҹҗжўқиЎ—жҷҜжӢҚеҲ°пјҢжҲ‘е°ұеҸҜд»Ҙи·ҹеҠүе°Ҹжқұз”ўз”ҹй—ңдҝӮпјҢеӣ зӮәйӮЈе°ұжҳҜд»–зҡ„з”ҹжҙ»гҖӮдҪҶиҰҒжҖҺйәјжЁЈзӣҙжҺҘи®“д»–и·ҹзҸҫе ҙз”ўз”ҹй—ңдҝӮпјҢе°ұиҰҒеҫҲе°ҸеҝғгҖӮе…¶еҜҰжҲ‘д№ҹжӢҚеҲ°еҫҲеӨҡпјҢдҪҶзңӢиө·дҫҶе°ұдёҚе°ҚпјҢе®ғеҸҚиҖҢжІ’й—ңдҝӮгҖӮиӯ¬еҰӮе°ҸжқұиӘӘпјҡгҖҢдёүеҚҒе№ҙйҒҺеҺ»дәҶпјҢйҖҷдёҖж¬ЎпјҢжҲ‘жұәе®ҡеӣһ家гҖӮгҖҚд»ЈиЎЁд»–дёүеҚҒе№ҙжІ’еңЁйҮ‘еҹҺз”ҹжҙ»дәҶгҖӮеҠүе°ҸжқұжҳҜеҖӢдёҖејөз•«жӢҚиіЈеғ№еӨҡе°‘йҢўзҡ„畫家пјҢеӣһеҲ°е®¶й„үпјҢд»–зҡ„йҖҷдәӣжңӢеҸӢжңүдёҖеҖӢжңҲиіәдёҚеҲ°дёғзҷҫе…ғе·ҘиіҮзҡ„дәәпјҢе…©ж–№ж”ҫеңЁдёҖиө·пјҢе°ҚжҜ”жҖ§е·Із¶“еҫҲеј·дәҶпјҢ當дҪ еҶҚжӢҚд»–и·ҹз’°еўғд№Ӣй–“зҡ„ж„ҹиҰәпјҢеҸҚиҖҢжңғиҰәеҫ—ж јж јдёҚе…ҘпјҢеҢ…жӢ¬дәәзҡ„жЁЈиІҢгҖҒй—ңеҝғзҡ„дәӢжғ…пјҢе°ұдёҚдёҖжЁЈгҖӮжҲ‘еҖ‘з•ўз«ҹдёҚжҳҜиҰҒиЁҺи«–йҖҷжЁЈзҡ„畫家еӣһеҲ°е®¶й„үжңғжҖҺжЁЈпјҢеҸҜиғҪжҳҜеӣ зӮәйҖҷжЁЈпјҢжүҖд»ҘгҖҠйҮ‘еҹҺе°ҸеӯҗгҖӢи·ҹеҠүе°Ҹжқұе…¶еҜҰжҳҜжңүдёҖй»һжҠҪйӣўзҡ„пјҢеңЁз’°еўғдёҠпјҢиӯ¬еҰӮиӘӘжҲ‘жІ’жңүжӢҚд»–еңЁиЎ—дёҠйҒҠи•©пјҢд»–е…¶еҜҰжңүпјҢдҪҶжҲ‘жІ’з”ЁпјҢеӣ зӮәжҲ‘зҷјзҸҫдёҚе°ҚпјҢиҖҢдё”д№ҹдёҚжҳҜжҲ‘иҰҒиЁҺи«–зҡ„е…§е®№гҖӮ
йҖҷйғЁзүҮеӯҗжң¬дҫҶе°ұжҳҜдҫ·йҷҗеңЁйҮ‘еҹҺпјҢеҺҹе…Ҳд№ҹеңЁиҖғж…®жҳҜдёҚжҳҜеҢ—дә¬еҫ—жӢҚпјҢйҖҷеҖӢи—қ術家зҡ„е·ҘдҪңе®ӨгҖҒд»–зҡ„家гҖҒд»–зҡ„еӨӘеӨӘе’Ңе°Ҹеӯ©йғҪеңЁйӮЈпјҢдҪҶеӣ зӮәе‘ҪйЎҢе°ұжҳҜйҮ‘еҹҺпјҢе°ұжұәе®ҡи®“йҖҷеҖӢе‘ҪйЎҢдҫҶзҙ„жқҹжҲ‘еҖ‘дёҖй»һгҖӮдҪҶжҳҜ當дҪ жҠҠйҖҷеҖӢдәәж”ҫеҲ°йҖҷеҖӢз’°еўғиЈЎй ӯпјҢд»ҘзҸҫеңЁдҫҶзңӢ已經дёҚеӨ§е°ҚдәҶгҖӮиӯ¬еҰӮпјҢжңүдёҖж¬ЎпјҢд»–еңЁз•«з•«пјҢд»–зҲёзҲёдҫҶе…¬ең’жүҫд»–пјҢд»–е°ұжҸҗеүҚзөҗжқҹпјҢи·ҹзҲёзҲёеңЁе…¬ең’жҷғжҷғпјҢзңӢеҲ°дёҖеҖӢжү“иөӨиҶҠгҖҒе…Ёиә«еҲәйқ’зҡ„дәәпјҢеңЁйӮЈйӮҠжҠ“иҡұиңўиҰҒеӣһеҺ»зөҰйӣһеҗғпјҢе…¶еҜҰеҫҲжңүи¶ЈпјҢжҲ‘д№ҹжңүжӢҚпјҢдҪҶжҳҜеҶ·йқңдёҖзңӢпјҢд»–жңүй»һеғҸжҳҜй•·е®ҳеңЁиҰ–еҜҹпјҢзңӢиө·дҫҶеғҸеӨ–дәәгҖӮиҖҢдё”д»–е…¶еҜҰе№іеёёд№ҹеғҸдёҖеҖӢи—қ術家пјҢиӯ¬еҰӮиӘӘд»–иә«дёҠдёҖе®ҡеё¶зӣёж©ҹпјҢйҒҮеҲ°йҖҷзЁ®жңүи¶Јзҡ„дәӢд№ҹжҳҜжӢҝеҮәдҫҶдёҖзӣҙжӢҚпјҢи¬ӣи©ұзҡ„й«ҳеәҰд№ҹдёҚдёҖжЁЈгҖӮ

жӢҚйҖҷйғЁзүҮпјҢжӮЁиә«е…је°Һжј”е’Ңж”қеҪұпјҢйҖҷи·ҹзҙ”зІ№еҒҡе°Һжј”жҲ–ж”қеҪұзӣёијғиө·дҫҶпјҢжңғжңүд»ҖйәјжЁЈзҡ„е·®з•°пјҹ
е§ҡпјҡжҲ‘еңЁжӢҚгҖҠж„ӣйә—зөІзҡ„йҸЎеӯҗгҖӢе°ұйҒҮеҲ°йҖҷеҖӢе•ҸйЎҢпјҢйҖҷжҳҜе…©еҖӢеҫҲз—ӣиӢҰзҡ„дҪҚзҪ®гҖӮеҰӮжһңдҪ иҮӘе·ұжңүеҖӢж”қеҪұеё«жҲ–жңүеҖӢе°Һжј”пјҢйӮЈжҳҜдёҚдёҖжЁЈзҡ„пјҢе…©ж–№иӮҜе®ҡжҳҜжҠ“еҲ°жҷӮй–“дёҖзӣҙиҒҠдёҖзӣҙиҒҠпјҢеҲ°еә•иҰҒд»ҖйәјпјҢеүӣеүӣжҲ‘еҖ‘йӮЈеҖӢе°ҚдёҚе°ҚпјҢиҰҒдёҖзӣҙи©ҰгҖӮйҖҷе…¶еҜҰжҳҜдёҖеҖӢгҖҢзөҗж§ӢгҖҚе’ҢгҖҢи§Јж§ӢгҖҚзҡ„йҒҺзЁӢпјҢе°Һжј”жҳҜдёҖзӣҙзөҗж§ӢпјҢйҖҷеҖӢиҰҒпјҢйӮЈеҖӢиҰҒпјӣеҸҜжҳҜе°Қж”қеҪұдҫҶи¬ӣдёҚдёҖжЁЈпјҢж”қеҪұжҳҜи§Јж§ӢпјҢиҰҒи§Јж§ӢжүҚиғҪжӢҚеҲ°е°Һжј”иҰҒзҡ„жқұиҘҝпјҢдёҚеҸҜиғҪеғҸе°Һжј”йӮЈжЁЈеӨ©йҰ¬иЎҢз©әпјҢйғҪеҫ—иў«жҠҖиЎ“еҢ…еҗ«дҪҸгҖӮиӯ¬еҰӮи«ҮеҲ°жҹҗзЁ®жғ…з·’пјҢд№ҹеҫ—иҰҒжңүйӮЈзЁ®е…үжүҚйҖ жҲҗеҫ—дәҶйӮЈзЁ®жғ…з·’пјҢж”қеҪұеҸҜд»Ҙи·ҹе°Һжј”жәқйҖҡпјҡгҖҢдҪ жғіиҰҒйҖҷеҖӢжғ…з·’пјҢйӮЈжҲ‘еҖ‘еҸҜдёҚеҸҜд»ҘеӮҚжҷҡжӢҚпјҢжҲ–жҳҜзӘ—йӮҠзөҰжҲ‘жү“еҖӢзҮҲеҸҜд»Ҙе—ҺпјҹгҖҚ
жӢҚгҖҠйҮ‘еҹҺе°ҸеӯҗгҖӢжҷӮпјҢжҲ‘жІ’жңүйӮЈеҖӢи«ҮеӨ©зҡ„йҒҺзЁӢпјҢеЈ“еҠӣж №жң¬жІ’ең°ж–№жҺ’гҖӮ當еҲқжӢҚгҖҠж„ӣйә—зөІзҡ„йҸЎеӯҗгҖӢпјҢзӣЈиЈҪжҳҜдҫҜе°ҺпјҢжҲ‘е°ұе•ҸдҫҜе°ҺеҸҜдёҚеҸҜд»ҘжүҫеҖӢж”қеҪұеё«пјҢд»–иӘӘпјҡгҖҢдҪ е°ұж”қеҪұеё«дәҶпјҢдҪ жүҫд»Җйәјж”қеҪұеё«гҖӮжІ’жңүдәәеҸҜд»Ҙ當дҪ ж”қеҪұеё«пјҢдҪ иҮӘе·ұжӢҚе•ҰгҖӮгҖҚиҖҒеӨ§дёӢжҢҮд»ӨдәҶпјҢдҪ е°ұжІ’иҫҰжі•пјҢеҸӘеҘҪиҮӘе·ұжӢҚпјҢи·ҹиҮӘе·ұе°Қи©ұгҖӮйӮЈжҷӮеҖҷеЈ“еҠӣжӣҙеӨ§пјҢеңЁеӯёзҝ’жҖҺйәјеҗҢжҷӮйқўе°ҚйҖҷе…©еҖӢе·ҘдҪңгҖӮжӢҚе»Је‘ҠжҷӮжҲ‘еёёиә«е…јйҖҷе…©еҖӢиҒ·еӢҷпјҢдҪҶеӣ зӮәжҷӮй–“зҹӯпјҢжүҖд»ҘеЈ“еҠӣжІ’жңүжӢҚй•·зүҮдҫҶеҫ—еӨ§гҖӮ
дҪҶжҳҜд»ҘзҙҖйҢ„зүҮдҫҶи¬ӣпјҢ當дёҖеҖӢе°Һжј”жңүжғіжі•зҡ„жҷӮеҖҷпјҢеҶҚиҰҒжұӮж”қеҪұеҺ»жӢҚпјҢжңүжҷӮеҖҷжҷӮй–“еёёеёёйҒҺдәҶпјҢеҰӮжһңжӢҚзҙҖйҢ„зүҮиҮӘе·ұиғҪе№№ж”қеҪұзҡ„и©ұпјҢжңғеҶҚжә–дёҖй»һпјҢеӣ зӮәж”қеҪұж©ҹжӢҝиө·дҫҶзҡ„жҷӮж©ҹи·ҹдҪ жғізҡ„жҳҜдёҖжЁЈзҡ„гҖӮ

гҖҠйҮ‘еҹҺе°ҸеӯҗгҖӢзҡ„й…ҚжЁӮжҘөзӮәжӮ жҸҡеӢ•иҒҪпјҢйҖҷж¬ЎжҳҜи·ҹжһ—еј·еҗҲдҪңпјҢд»–д№ҹжҳҜдҫҜе°Һй•·жңҹеҗҲдҪңзҡ„йҹіжЁӮдәәгҖӮиғҪеҗҰи«ӢжӮЁи«Үи«Үи·ҹд»–еҗҲдҪңзҡ„經驗пјҹ
е§ҡпјҡе…¶еҜҰжҲ‘жң¬дҫҶеңЁй җдј°йҮ‘йҰ¬зҚҺе…ҘеңҚжҷӮпјҢй җдј°зҡ„жҳҜйҹіжЁӮпјҢеӣ зӮәжүҖжңүзңӢйҒҺзҡ„дәәйғҪи·ҹжҲ‘иӘӘйҹіжЁӮеӨӘеҘҪдәҶгҖӮжһ—еј·дёҖзӣҙйғҪжҳҜжҲ‘еҖ‘зҡ„йҹіжЁӮзёҪзӣЈпјҢд»–жңғ幫жҲ‘еҖ‘еҲӨж–·йҹіжЁӮжҳҜд»ҖйәјиӘҝеӯҗжҲ–дәӨз”ұд»ҖйәјдәәдҫҶеҒҡгҖӮгҖҠйҮ‘еҹҺе°ҸеӯҗгҖӢжҳҜжҲ‘иҮӘе·ұжӢҚгҖҒиҮӘе·ұж”қеҪұгҖҒйӮ„еҢ…жӢ¬иҮӘе·ұеүӘжҺҘпјҢиҮӘе·ұеүӘжҺҘжҷӮеёёеёёжңғе…ҲеҺ»жүҫзҗҶжғізҡ„йҹіжЁӮгҖӮжҲ‘еҺ»йҮ‘еҹҺеүҚпјҢжңүе…Ҳж•ҙзҗҶжҲ‘иҰҒзҡ„йҹіжЁӮеңЁplayerиЈЎй ӯпјҢеёёеёёеҫ—иҒҪпјҢеҝғжғ…дёҚеҘҪгҖҒеЈ“еҠӣеӨ§жҲ–жүҫдёҚеҲ°ж„ҹиҰәзҡ„жҷӮеҖҷеҫ—иҒҪпјҢеӣ зӮәйӮЈдәӣйҹіжЁӮжҳҜдҪ зҗҶжҷәжүҫйҒҺзҡ„гҖӮеӣһй ӯеңЁеүӘжҺҘзҡ„жҷӮеҖҷпјҢеңЁдҪ йӮ„жІ’жңүйҹіжЁӮжҷӮпјҢ當然д№ҹжңғжҠҠйҖҷдәӣйҹіжЁӮжӢҝдҫҶе…Ҳз”ЁпјҢжүҖд»ҘдҪ жңғиў«йӮЈеҖӢйҹіжЁӮе®ҡеһӢгҖӮйҖҷжҷӮжһ—еј·жүҚжңғйҖІдҫҶпјҢе°ұд»–зҡ„ж„ҹиҰәеҒҡйҹіжЁӮзөҰдҪ пјҢйӮЈжҷӮдҪ жңғиҰәеҫ—пјҡгҖҢдёҚжҳҜйҖҷжЁЈпјҢдёҚжҳҜйҖҷзЁ®ж„ҹиҰәе•ҰгҖӮгҖҚ然еҫҢи·ҹд»–жәқйҖҡиҮӘе·ұзҡ„ж„ҹиҰәгҖӮжһ—еј·еҖӢжҖ§еҫҲеҘҪпјҢдёҚжңғйӮЈйәје …жҢҒпјҢе°ұ幫дҪ ж”№пјҢиӘҝж•ҙе№ҫж¬ЎдёӢдҫҶпјҢйҹіжЁӮеҚ»е·Із¶“зҲӣеҲ°дёҚиЎҢдәҶгҖӮжҲ‘е°ұеҫҲз„Ұж…®пјҢеҝғжғіжҳҜдёҚжҳҜжәқйҖҡжңүе•ҸйЎҢпјҢеӣ зӮәжҲ‘дёҚеӨӘжңғи¬ӣи©ұгҖӮеӣһй ӯеҸӘеҘҪжҠҠ第дёҖж¬Ўзҡ„йҹіжЁӮжӢҝеҮәдҫҶиҒҪпјҢеҶ·йқңдёҖиҒҪпјҢзҷјзҸҫеҘҪеғҸе°ҚдәҶпјҢе…¶еҜҰд»–зөҰдҪ зҡ„第дёҖж¬Ўе°ұжҳҜе°Қзҡ„пјҢдҪ иҮӘе·ұдёҚзҹҘйҒ“пјҢиў«иҮӘе·ұзҡ„йҹіжЁӮйҺ–жӯ»дәҶгҖӮ
еғҸдҫҜе°Һи·ҹжһ—еј·еҗҲдҪңзҡ„жЁЎејҸе°ұжҳҜпјҢд№ҫи„ҶжҠҠдәәйҖҒеҲ°йӮЈйӮҠеҺ»пјҢжүҖд»Ҙжһ—еј·д№ҹжңүеҺ»йҮ‘еҹҺдёҖи¶ҹпјҢжҲ‘е°ұе®үжҺ’и§Җе…үиЎҢзЁӢпјҢи®“д»–иө°йҒҺжҲ‘ж„ҹиҰәдёҚйҢҜзҡ„ең°ж–№пјҢе°ұжңүд»–иҮӘе·ұзҡ„ж„ҹиҰәгҖӮд»–зҡ„йҹіжЁӮе…¶еҜҰеҫҲжә–пјҢеҫҲеҺІе®іпјҢд»–еҺ»иҳҶи‘Ұи•©йӮЈеҖӢең°ж–№зңӢйҒҺпјҢеҜ„зөҰжҲ‘еҖ‘зҡ„第дёҖйҰ–жӣІзӣ®е°ұжҳҜгҖҲи‘ҰеЎҳгҖүгҖӮжҲ‘иҰәеҫ—д»–зҡ„йҹіжЁӮ已經еҒҡеҲ°зҘһ經裡йқўеҺ»дәҶгҖӮеҫҢдҫҶжҲ‘зңҹзҡ„ж”ҫжЈ„и·ҹд»–жәқйҖҡпјҢеӣ зӮәзҷјзҸҫйҹіжЁӮд»–зңҹзҡ„жҜ”дҪ еҺІе®іпјҢеҰӮжһңд»–жңүж„ҹиҰәпјҢе°ұзңҹзҡ„з”ӯиӘӘд»ҖйәјдәҶгҖӮ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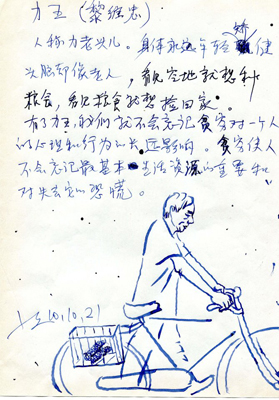
жңҖеҫҢпјҢиҰҒи«Ӣе°Һжј”жҺЁи–ҰгҖҠж”ҫжҳ йҖұе ұгҖӢзҡ„и®ҖиҖ…дёҖеҖӢйқһзңӢжң¬зүҮдёҚеҸҜзҡ„зҗҶз”ұгҖӮ
е§ҡпјҡеҠүе°ҸжқұжҳҜдёӯеңӢж•ёдёҖж•ёдәҢзҡ„畫家пјҢе…үйҖҷй»һе°ұйқһзңӢдәҶгҖӮзҙҖйҢ„зүҮе…¶еҜҰжҳҜж„ҲжІүж„ҲйҰҷпјҢжҲ‘ж•ўжү“еҢ…зҘЁпјҢдә”е№ҙеҫҢдҫҶзңӢгҖҠйҮ‘еҹҺе°ҸеӯҗгҖӢйӮ„жҳҜеҫҲеҘҪзңӢпјҢеӣ зӮәйҖҷжҳҜдёҖеҖӢ畫家зҡ„жүҖжҖқжүҖжғіпјҢжІ’жңүе№ҙйҷҗзҡ„е•ҸйЎҢгҖӮ
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