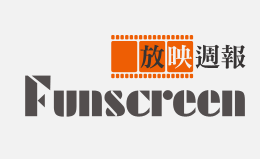ж®ҳйҹҝжҢҮж¶үдәӢ件еҫҢзәҢзҡ„еӣһиҒІиҲҮж“ҙ延пјҢз©ҚжҘөйқўеңЁж–јж—Ҙеёёз”ҹжҙ»зҡ„еүөеҷӘиҲҮж•…дәӢеҶҚж•ҳиӘӘпјҢеӣӣж®өйҢ„еғҸгҖҲйҷӘдјҙж•ЈиЁҳгҖүгҖҒгҖҲзЁ®жЁ№зҡ„дәәгҖүгҖҒгҖҲиў«жҮёзҪ®зҡ„жҲҝй–“гҖүгҖҒгҖҲд№ӢеҫҢиҲҮд№ӢеүҚгҖүеҲҶеҲҘйҒёж“ҮејөиҠіз¶әгҖҒйҷўж°‘гҖҒйҷёй…ҚгҖҒеҲ‘еӢҷжүҖж”ҝжІ»зҠҜе№ҪйқҲдҪңзӮәеҲҮе…Ҙй»һпјҢжӮЁжҖҺйәјжҖқиҖғйҖҷе№ҫеҖӢи»ёз·ҡе’ҢзҸҫе ҙзҡ„й—ңдҝӮпјҹ
йҷіз•Ңд»ҒпјҡзҸҫе ҙжңүеҫҲеӨҡж„ҸжҖқпјҢйҒӢеӢ•зҡ„зҸҫе ҙжҳҜйӮЈдёҖеҲ»зҡ„иғҪйҮҸзҲҶзҷјпјҢиҒҡйӣҶзҡ„зҜҖй»һгҖӮзҸҫе ҙд№ҹйқһеёёиӨҮйӣңпјҢдё»ж•ҳдәӢд№ӢеӨ–йӮ„жңүж¬ЎиҰҒгҖҒе‘ЁйӮҠзҡ„дәәпјҢйҒӢеӢ•зҡ„жҖҘиҝ«жҖ§д№ӢеӨ–жңүеҫҲеӨҡеӯҗе•ҸйЎҢгҖӮзҸҫе ҙзҡ„ж„Ҹзҫ©жңғдёҖзӣҙж”№и®ҠпјҢ1927е№ҙд№ҹжҳҜдёҖеҖӢзҸҫе ҙпјҢ當ж—Ҙжң¬з•«иЁӯиЁҲең–гҖҒжұәе®ҡиҰҒи“ӢйҖҷеә§зҷӮйӨҠйҷўжҷӮпјҢе°ұ已經註е®ҡдәҶеҫҢйқўзҡ„дәӢгҖӮеҢ…жӢ¬зҫҺжҸҙжҷӮжңҹзҡ„DDSи—Ҙзү©йҖ жҲҗеӨ§йҮҸйҷўж°‘иҮӘж®әпјҲиЁ»3пјүпјҢжүҖжңүдәӢжғ…йғҪзӣёдә’й—ңйҖЈпјҢзҸҫе ҙдёҚеғ…жҳҜеӨҡеұӨж¬Ўзҡ„гҖҒд№ҹжҳҜдёҖзӣҙеңЁжөҒи®Ҡзҡ„гҖӮйӮЈйәјпјҢзҸҫе ҙеҲ°еә•еңЁе“ӘиЈЎпјҹ當йҒӢеӢ•йҖІе…Ҙз“¶й ёгҖҒдҪҺжҪ®пјҢйӮ„жңүд»ҖйәјеҸҜиғҪжҖ§пјҹеҰӮжһңи—қиЎ“йӮ„жңүй»һз”ЁпјҢйҖҷе°ұжҳҜжүҖи¬ӮжғіеғҸеҠӣгҖҒеүөдҪңи©ІеҺ»еҒҡзҡ„гҖӮ
зҸҫд»ЈжҖ§зҷјеұ•дёҚжҳҜзө•е°ҚиІ йқўпјҢ當然зҷӮйӨҠйҷўгҖҒзӣЈзҚ„д»ЈиЎЁијғиІ йқўзҡ„дёҖз’°пјҢдҪҶйҒӢеӢ•йҷӨдәҶдҝқиЎӣжЁӮз”ҹгҖҒеҸҚзҷјеұ•дё»зҫ©пјҢиғҪдёҚиғҪеңЁжӯЈеҸҚеҗҲзҡ„иҫҜиӯүйӮҸијҜд№ӢеӨ–й–ӢеҮәе…¶д»–зҡ„жғіеғҸпјҲжҲ‘зЁұд№ӢзӮәгҖҢйқһеҗҲгҖҚпјүпјҢдҪңзӮәжңӘдҫҶзҡ„еҸғз…§пјҹжЁӮз”ҹйҒӢеӢ•иҮӘ然жңғиө°еҗ‘еҸҚзҷјеұ•дё»зҫ©пјҢдҪҶзҷјеұ•дё»зҫ©иҲҮеұ…ж°‘зҡ„зҷјеұ•ж…ҫжңӣжІ’жңүдёҚе°ҚпјҢеҸӘжҳҜиў«еҲ©з”ЁдәҶгҖӮжҲ‘еҖ‘жҠҠжҚ·йҒӢи·ҹжҚ·йҒӢеұҖй•·з¶ҒеңЁдёҖиө·пјҢйӮЈжҳҜж”ҝе®ўе№№зҡ„дәӢпјҢдҪҶеҫҲе®№жҳ“и®“йҒӢеӢ•йҷ·е…ҘзӮәдәҶдҝқиЎӣжЁӮз”ҹиҖҢгҖҢеҸҚе°Қзҷјеұ•гҖҚзҡ„йӮҸијҜиЈЎгҖӮзҸҫеңЁйҡ”дәҶйҖҷйәјд№…пјҢжЁӮз”ҹйҒӢеӢ•еҸҜд»Ҙеё¶зөҰжҲ‘еҖ‘д»ҖйәјпјҹеҰӮжһңдёҚжҳҜеҸҚзҷјеұ•пјҢзҷјеұ•йӮ„жңүе№ҫзЁ®жЁЎеһӢе’ҢеҸҜиғҪпјҹ
еҒҡгҖҠе№ёзҰҸеӨ§е»ҲIгҖӢжҷӮпјҢжңүеӨ©жҷҡдёҠжҲ‘и·ҹиҠіз¶әеңЁжЁӮз”ҹпјҲиЁ»4пјүпјҢжҲ‘е•ҸеҘ№пјҢеј·еҲ¶й©…йӣўзҷјз”ҹжҷӮеҰіеңЁе“ӘиЈЎпјҹ當жҷӮеҘ№ж—ўеңЁжҠ—зҲӯзҸҫе ҙпјҢеҸҲеңЁеұӢе…§йҷӘйҷўж°‘дёҖиө·зңӢйӣ»иҰ–иҪүж’ӯпјҢеҫһй ӯеҲ°е°ҫжІ’жңүеҮәдҫҶпјҢиҖҢеј·жӢҶе°ұзҷјз”ҹеңЁд»–еҖ‘еүҚйқўпјҢеҸӘжңүдёҖзүҶд№Ӣйҡ”гҖӮйӮЈжЈҹеұӢеӯҗжІ’жңүиў«жӢҶпјҢеүҚйқўжҳҜжҚ·йҒӢе·Ҙең°еңҚзүҶпјҢеҶҚеүҚйқўе°ұжҳҜйҷ·дёӢеҺ»зҡ„еқЎеқҺгҖӮжҲ‘еҖ‘з«ҷеңЁеқЎеқҺйӮҠпјҢдё»иҰҒжҠ—зҲӯзҡ„зҸҫе ҙ已經ж¶ҲеӨұпјҢи®ҠжҲҗдёҖеҖӢе·ЁеӨ§зҡ„жҙһпјҢиҖҢеҘ№еҫ…и‘—зҡ„еұӢеӯҗйӮ„еңЁгҖӮеҰӮжһңжҷҡдёҠз«ҷеңЁйӮЈиЈЎпјҢдҪ жңғзңӢеҲ°ж–Ҫе·Ҙдёӯзҡ„е·ҘдәәгҖҒеӨңй–“зҡ„зҮҲгҖҒе·ҘеҜ®е®ҝиҲҚпјҢдҪ жңғзҹҘйҒ“йӮЈжҳҜдёҖеҖӢиҮЁжҷӮзӢҖж…ӢпјҢе®Ңе·ҘеҫҢе°ұжңғж¶ҲеӨұпјҢеғҸдёҖеЎҠз•«еёғдёҚж–·еңЁдёҠйқўеЎ—жҠ№пјҢең°иІҢдёҖзӣҙи®ҠеҢ–пјҢйҖЈжҢҮиӘҚйғҪз„Ўжі•гҖӮйҖҷйәјеӨҡдәәеҸғиҲҮйҒҺжЁӮз”ҹпјҢдҪҶжүҖжңүз—•и·ЎеҰӮд»Ҡе№ҫд№ҺйғҪдёҚиҰӢдәҶгҖӮ
иҠіз¶ә18жӯІй–Ӣе§ӢеҸғиҲҮжЁӮз”ҹдҝқз•ҷйҒӢеӢ•пјҢиҮід»Ҡ8е№ҙпјҢеҘ№еёёеёёиӘӘеҘ№еңЁеҒҡжӘ”жЎҲпјҢжүҖи¬ӮжӘ”жЎҲжҳҜдёҖеӨ§з–ҠеҘҮжҖӘзҡ„е»ўзҙҷгҖҒе ұзҙҷпјҢдәӮдёғе…«зіҹеҜ«и‘—йҷӘдјҙйҷўж°‘зҡ„ж„ҹжғіпјҢз•«дәҶеҫҲеӨҡзҙ жҸҸпјҢжІ’жңүжҷӮй–“й ҶеәҸпјҢй–ұи®ҖжҷӮж–№еҗ‘еҝ…й ҲиҪүдҫҶиҪүеҺ»пјҢзҙҷејөзҝ»йҒҺдҫҶиғҢйқўйӮ„жңүеӯ—пјҢжңүжҷӮеҖҷеҸҲзӘҒ然жҠ„дёҖж®өе“Іеӯёе®¶зҡ„и©ұгҖӮжҲ‘и®ҖдёҚжҮӮпјҢе•ҸеҘ№пјҢеҘ№зңӢдёҖзңӢиӘӘпјҡгҖҢе№№пјҒжҲ‘д№ҹзңӢдёҚжҮӮгҖӮгҖҚ2008е№ҙеј·жӢҶйҒҺеҫҢдәәжјёжјёи®Ҡе°‘пјҢеҸӘжңүдёҖдәӣжЁӮйқ’йӮ„з•ҷи‘—пјҢиҠіз¶әеңЁжЁӮз”ҹж··дәҶ6е№ҙпјҢеёёиў«дәә笑иӘӘд»Җйәјд№ҹжІ’з”ҹз”ўеҮәдҫҶгҖӮжҲ‘жңғжғіпјҢйӮЈдёҖеӨ§з–ҠжӘ”жЎҲж„Ҹе‘іи‘—д»Җйәјпјҹ
йҖҷиЈЎйқўжңүи¶Јзҡ„ең°ж–№жҳҜпјҢеҘ№еңЁйҒӢеӢ•иЈЎйқўж №жң¬дёҚйҮҚиҰҒпјҢеҘ№дёҚжҳҜеҸҜд»ҘеҸғиҲҮиЁҺи«–зҡ„дәәгҖӮеҘ№и·‘еҺ»йҷӘдјҙйҷўж°‘пјҢдё”жҢ‘дәҶдёҚжҳҜиҮӘж•‘жңғзҡ„дәәгҖӮйҷӘдјҙеҚҠе№ҙеӨҡпјҢжӘ”жЎҲиЈЎеҜ«дәҶеҫҲеӨҡз‘ЈзўҺзҡ„дәӢпјҢйҷўж°‘йҒҺйҖқеүҚеҫҢеҸҚиҖҢжІ’жңүзҙҖйҢ„пјҢйҡ”дәҶеҫҲд№…жүҚеҸҲй–Ӣе§ӢеҜ«йӮЈеҘҮжҖӘзҡ„жӘ”жЎҲгҖӮеҰӮжһңеҸҜд»ҘеҮәзүҲпјҢжҲ‘иӘҚзӮәжҳҜзЁ®йј“еӢөпјҢеӣ зӮәжҲ‘еҖ‘еӨӘжҖ•еҺ»и«Үи«–дё»ж•ҳдәӢд№ӢеӨ–зҡ„еҗ„зЁ®йқўеҗ‘гҖӮ
йҒӢеӢ•дё»ж•ҳдәӢгҖҒйҷўж°‘еҸЈиҝ°еҸІгҖҒи«–ж–ҮжҲ–зҙҖйҢ„еҪұеғҸеҹәжң¬дёҠйғҪеңЁдёҖеҖӢзҜ„еңҚе…§пјҢжІ’жңүйҖІе…ҘеҸЈиҝ°еҸІзҡ„дәәж°ёйҒ з„Ўжі•иў«ж•ҳиӘӘгҖӮеҫҲеӨҡжЁӮйқ’йғҪжҳҜеңЁеӨ§еӯёгҖҒз ”з©¶жүҖжҷӮиў«йҒӢеӢ•е•ҹи’ҷпјҢд№ҹ第дёҖж¬ЎзңӢеҲ°йҒӢеӢ•иЈЎзҡ„иӨҮйӣңжҖ§пјҢд»–еҖ‘жҖҺйәјиҝ°иӘӘиҮӘе·ұзіҫзәҸзҡ„еҖӢдәә經驗пјҹжҲ‘е°ҮејөиҠіз¶әзҡ„е…§еҝғзҚЁзҷҪгҖҒиЁҳжҶ¶жӢјең–зЁұзӮәгҖҢж„ҹжҖ§жӘ”жЎҲгҖҚпјҢеҸҜд»ҘжҠҳе°„еҮәдёҖд»Јдәәе°ҚйҒӢеӢ•зҡ„еҗ„зЁ®жғіеғҸгҖӮжҲ‘йҒёж“ҮиҠіз¶әпјҢеӣ зӮәйӮЈжҳҜжңҖж”ҝжІ»дёҚжӯЈзўәзҡ„гҖӮеҘ№еҫһй ӯеҲ°е°ҫйғҪжІ’жңүеҠ е…ҘжЁӮйқ’пјҢдҪҶйҖҷ件дәӢзўәеҜҰеҪұйҹҝдәҶеҘ№зҡ„дёҖз”ҹгҖӮеҘ№йҷӘдјҙеӨ–зңҒиҖҒдјҜдјҜпјҢдҪҶй„үйҹіеҫҲйҮҚпјҢе…©дәәе…¶еҜҰдёҚеӨӘиғҪжәқйҖҡгҖӮйҒӢеӢ•дёӯеҫҲеӨҡжқұиҘҝжңғеҝ«йҖҹйҖІе…ҘдёҖзЁ®ж”ҝжІ»жӯЈзўәзҡ„и«Үжі•пјҢеҘ№зҡ„жӘ”жЎҲж•ҙзҗҶзўәеҜҰжғіжҺҘдёҠдёҖдәӣжқұиҘҝпјҢдҪҶдёҚзҹҘйҒ“жҖҺйәјжҺҘпјҢжҒ°жҒ°еӣ зӮәйҖҷжЁЈпјҢжңғй•·еҮәдёҖдәӣз•°иіӘзҡ„жқұиҘҝгҖӮ
йҷўж°‘зЁ®жЁ№д№ҹеҫҲжңүж„ҸжҖқпјҢ800еӨҡжЈөжЁ№дҝқиӯ·дәҶйҖҷдәӣдәәгҖҒйҖҷеҖӢйҷўеҚҖ80е№ҙпјҢжңүеҫҲз©ҚжҘөзҡ„ж„Ҹзҫ©пјҢд№ҹжҳҜеҸҰдёҖзЁ®зҷјеұ•пјҢеҸӘжҳҜиҲҮйҷ„иҝ‘еұ…ж°‘зҡ„зҷјеұ•дёҚеҗҢпјҢжҳҜе…©зЁ®жғіеғҸзҡ„й¬ҘзҲӯгҖӮзЁ®жЁ№йҖҷ件дәӢж„Ҹзҫ©и »иӨҮйӣңзҡ„пјҢеӣ зӮәиў«йҷҗеҲ¶иЎҢеӢ•пјҢд»–еҖ‘д№ҹиЁұеӣ зӮәз„ЎиҒҠпјҢжҲ–еҸӘжҳҜй•·е®ҳиҰҒд»–еҖ‘зЁ®пјӣзёҪд№ӢпјҢд»–еҖ‘зЁ®дәҶ800еӨҡжЈөжЁ№пјҢз„ЎеҝғжҸ’жҹіжҹіжҲҗи”ӯпјҢжҜҸжЈөйғҪй•·еҫ—еҫҲеӨ§пјҢжЁ№еҸҜд»Ҙж°ҙеңҹдҝқжҢҒпјҢдҪҶд№ҹжҳҜеҸҰдёҖзЁ®з”ҹе‘Ҫзҷјеұ•гҖӮ
жҲ‘еҖ‘жүҫеҜҢеӯҗе§ҠеҺ»еұұдёҠе”ұжӯҢпјҢи¬ӣеҘ№иҮӘе·ұзҡ„ж•…дәӢгҖӮеҘ№йҢ„е®ҢдёҖйҰ–пјҢжҲ‘еҺҹжң¬иҰәеҫ—дёҚйҢҜпјҢжғіиӘӘеҶҚеӨҡжӢҚдёҖеҖӢtakeпјҢзөҗжһң第дәҢж¬Ўе”ұеҫ—е®Ңе…ЁдёҚеҗҢпјҢеӣ зӮәеҘ№зңӢиҰӢе·Ҙең°е’ҢеҒңи»Ҡе ҙпјҢжғіеҲ°е®¶д»ҘеүҚе°ұеңЁйӮЈиЈЎгҖӮжҲ‘иҒҪдёҚжҮӮжӯҢи©һпјҢеҘ№д№ҹеҝҳиЁҳиҮӘе·ұе”ұдәҶд»ҖйәјпјҢе®Ңе…ЁжҳҜеҚіиҲҲгҖӮеҸӘжңүиҒІйҹіпјҢжІ’жңүж–Үеӯ—пјҢжҲ‘иҰәеҫ—йҖҷжЁЈеҸҚиҖҢдёҚйҢҜпјҢиӘһиЁҖжӯӨжҷӮи®Ҡеҫ—еғөзЎ¬гҖӮжҲ‘еҖ‘зңҹжӯЈиҰҒиӘӘзҡ„и©ұпјҢиӘһиЁҖ已經дёҚи¶ід»ҘиЎЁйҒ”гҖӮйӮЈзһ¬й–“жҲ‘зҹҘйҒ“йҖҷжүҚжҳҜе°Қзҡ„пјҢеҜҢеӯҗе§ҠеҒҡдәҶдёҖ件當代и—қиЎ“дҪңе“ҒгҖӮеҜҢеӯҗе§ҠдёҠеұұйӮЈе ҙжҲІжҳҜеңЁеӨ©еҫ®дә®гҖҒй»ғжҳҸзҡ„жҷӮеҖҷпјҢжҲ–иҖ…иҠұеҫҲеӨҡжҷӮй–“зӯүеҫ…йҷ°еӨ©пјҢж”қеҪұеё«жӢҝи‘—ж”қеҪұж©ҹеҫһеҒҙйқўи·ҹи‘—еҘ№и·‘жӯҘпјҢеүҚйқўжңүеҖӢдәәж“Ӣи‘—йҳІжӯўеҘ№йЈҶи»ҠгҖӮйҖҷдәӣе…¶еҜҰжҲ‘йғҪдёҚжҮүи©Іи¬ӣзҡ„……гҖӮ
жӢҚж”қйҷёй…ҚпјҢжҳҜеӣ зӮәжҲ‘еҺҹжғіжӢҚйҷўиЈЎзҡ„еӨ–зұҚзңӢиӯ·пјҢдҪҶж¶үеҸҠйҡұз§ҒжІ’иҫҰжі•жӢҚгҖӮйҒҺеҺ»жӢҚгҖҠеёқеңӢйӮҠз•ҢгҖӢжҷӮпјҢиӘҚиӯҳеҫҲеӨҡеңЁиҮЁзөӮз—…жҲҝзҡ„йҷёзұҚзңӢиӯ·пјҢеҘ№еҖ‘йғҪ經жӯ·йҒҺж–Үйқ©гҖӮеҪұзүҮдёӯеҘ№еҖ‘е”ұзҡ„жҳҜгҖҠзҷҪжҜӣеҘігҖӢпјҲиЁ»5пјүпјҢиӘӘзҡ„жҳҜең°дё»еЈ“иҝ«иҫІж°‘гҖҒеј·дҪ”ж°‘еҘізҡ„ж•…дәӢгҖӮеҘіеӯ©йқ’жў…з«№йҰ¬зҡ„ж„ӣдәәеҫҢдҫҶи·‘еҺ»з•¶и§Јж”ҫи»ҚпјҢеҘ№еҫҢдҫҶи·‘еҲ°еұұжҙһиЈЎпјҢи§Јж”ҫи»ҚеӣһдҫҶеҫҢеҘ№еҮәзҸҫдәҶпјҢеҚ»й•·дәҶж»ҝй ӯзҷҪй«®гҖӮйҖҷеңЁз•¶жҷӮи§Јж”ҫеҚҖиЈЎеҫҲжҝҖеӢөдәәеҝғпјҢиҫІеҘҙзңӢеҫ—еҫҲжҝҖеӢ•гҖӮжңүеҖӢйҷёй…Қе°ұдҪҸеңЁжЁӮз”ҹйҷ„иҝ‘пјҢеҚ»еҫһдҫҶдёҚзҹҘйҒ“жңүйҖҷжЁЈдёҖе ҙйҒӢеӢ•пјҢеҸҚйҒҺдҫҶжҲ‘еҖ‘д№ҹдёҚеӨӘдәҶи§ЈеҘ№еҖ‘иә«дёҠжңүеҸҰдёҖе ҙйҒӢеӢ•гҖӮж–Үйқ©жҷӮпјҢеҘ№е°Ҹеӯёе…ӯе№ҙзҙҡпјҢзҲ¶иҰӘиў«жҠ“пјҢеҘ№иў«йҒёзӮәе®ЈеӮійҡҠйҡҠй•·пјҢжҜҸеӨ©е”ұжӯҢи·іиҲһпјҢеӣ жӯӨеҘ№еҝғиЈЎжңүеҸҰдёҖе ҙйҒӢеӢ•гҖӮжүҖд»ҘпјҢи·Ҝдәәз”Ід№ҹжҳҜдёҖзЁ®зҸҫе ҙпјҢеҰӮжһңдҪ иҒҪеҫ—жҮӮйҖҷйҰ–жӯҢпјҢе°ұеҸҜд»ҘжҠҠе…©зЁ®йқ©е‘Ҫзҡ„ж„Ҹзҫ©йҖЈиө·дҫҶгҖӮйҖҷе ҙжҲІеҫһжё…жҷЁжӢҚеҲ°жҷҡдёҠпјҢжІ’жҺ’з·ҙе°ұзӣҙжҺҘдҫҶпјҢжҲ‘еҖ‘з§ҹдәҶе…¬еҜ“жҠҠзүҶжјҶй»‘гҖӮеҘ№еҖ‘еүҚдёҖжҷҡеңЁйҶ«йҷўеҫ№еӨңе·ҘдҪңпјҢеҚ»иӘӘдёҚжңғзҙҜпјҢеӣ зӮәе”ұи‘—йҖҷдәӣжӯҢпјҢеҘ№еҖ‘еҘҪеғҸеҸҲйғҪеӣһеҲ°дәҶйқ’жҳҘжңҹгҖӮ
иЁұеӨҡйҷёй…Қе«ҒдҫҶеҸ°зҒЈпјҢйғҪжҳҜе«ҒзөҰиҖҒиҠӢй ӯпјҢжңүзҡ„еңЁеӨ§йҷёзөҗйҒҺе©ҡпјҢеңӢзҮҹдјҒжҘӯз§ҒжңүеҢ–еҫҢжҲҗзӮәдёӢеҙ—е·ҘдәәпјҢеҫҢдҫҶеӣ з·Јйҡӣжңғе«ҒдҫҶеҸ°зҒЈгҖӮжҲ’еҡҙжҷӮд»ЈпјҢеҸ°зҒЈеЈ«е®ҳдёҚиғҪзөҗе©ҡпјҢеҫҢдҫҶжүҚи®“д»–еҖ‘зөҗе©ҡпјҢдҪҶд»–еҖ‘д№ҹдёҚеҸҜиғҪеҸ–еҸ°зҒЈеҘіеӯ©пјҢеӣ жӯӨеӨ§еӨҡеЁ¶еӨұе©ҡзҡ„йҷёзұҚеҘіеӯҗгҖӮзҸҫеңЁеҫҲеӨҡйҷёй…ҚиҒҡйӣҶеңЁжҰ®ж°‘д№Ӣ家пјҢеӣ зӮә經жӯ·ж–Үйқ©пјҢзҝ’ж…ЈиҮӘжҲ‘зө„з№”пјҢд№ҹжІ’жңүе…¶д»–зӨҫйҒӢеңҳй«”иҒІжҸҙд»–еҖ‘гҖӮд»–еҖ‘иҮӘе·ұзҷјеұ•еҮәеҘҪеӨҡзө„з№”ж”ҝй»ЁпјҢжңүеҸҰдёҖеҖӢзӢҖж…ӢпјҢйҷёй…Қд№ҹжңүеҫҲеӨҡдёҚеҗҢйЎһеһӢпјҢе°ұеғҸз—ІзҳӢз—…жӮЈиҖ…дёҖжЁЈпјҢиә«д»ҪеҫҲиӨҮйӣңгҖӮдё»ж•ҳдәӢд№ӢеӨ–зҡ„ж•…дәӢж №жң¬и«ҮдёҚе®ҢпјҢдҪҶжӢҚеҪұзүҮжІ’иҫҰжі•и«ҮйҖҷдәӣпјҢеҜ«е°ҸиӘӘеҸҜиғҪжҜ”ијғжңүи¶ЈгҖӮ
2008е№ҙйӣҷе№ҙеұ•жүҫжҲ‘еҒҡй—ңж–јжЁӮз”ҹзҡ„дҪңе“ҒпјҢжҲ‘жІ’зӯ”жҮүпјҢйҒӢеӢ•зҡ„жҷӮеҖҷеҒҡдҪңе“ҒеҫҲжҖӘпјҢд№ҹ幫дёҚдёҠеҝҷгҖӮ當йҖҷдәӣдәӢйғҪйҒҺеҺ»пјҢеӣ зӮәејөиҠіз¶әзҡ„й—ңдҝӮпјҢжүҚжңүеҖӢй»һжҺҘдёҠгҖӮжҲ‘еёёи¬ӣж®ҳйҹҝйҖҷеҖӢи©һпјҢдҪҶз«ҷеңЁжЁӮз”ҹеүҚзҡ„жҙһпјҢдҪ иӢҘжӢҝйәҘе…Ӣ風收йҹіпјҢжңғиҒҪеҲ°еұұи°·иҲ¬еҳ©еҳ©еҳ©зҡ„еӣһйҹіпјҢйӮЈж„ҹиҰәи »жҖӘзҡ„пјҢжңүй»һ科幻гҖӮ
гҖҲд№ӢеҫҢиҲҮд№ӢеүҚгҖүеҫһиҸҜе…үеҸ°еҢ—еҲ‘еӢҷжүҖиө°еҲ°жЁӮз”ҹпјҢж•ҙеҖӢйҒҺзЁӢйғҪжҳҜж®–ж°‘зҸҫд»ЈжҖ§пјҢдҪҶз„Ўи«–ж©«жҲ–зёұзҡ„жӯ·еҸІпјҢиЈЎйқўйғҪжңүеӨ§йҮҸзҡ„з©әзјәгҖӮжҲ‘еҖ‘ж°ёйҒ дёҚеҸҜиғҪжҗһжё…жҘҡйҖҷдәӣдәӢпјҢжӯ·еҸІж°ёйҒ еӨ§ж–јд»»дҪ•еҖӢдәәжҲ–и—қиЎ“е“ҒпјҢжҲ‘еҖ‘иғҪеҒҡзҡ„еҸӘжҳҜй–Ӣе•ҹж—ҒйӮҠзҡ„з©әй–“е ҙеҹҹгҖӮ
жӯӨдҪңд№ҹеӣһеҲ°еҺҹеқҖеңЁзҙҚйӘЁеЎ”ж—Ғж”ҫжҳ пјҢжӮЁеёҢжңӣйҖҷеҖӢиЎҢзӮәеҰӮдҪ•й–Ӣе•ҹе ҙеҹҹпјҢиҲҮ當дёӢзҸҫеҜҰдёӯзҡ„дәәз”ўз”ҹй—ңиҒҜпјҹ
йҷіз•Ңд»Ғпјҡе°ұжҳҜжҠҠжӣҫ經еҸғиҲҮйҒҺжҲ–дёҚиӘҚиӯҳзҡ„дәәиҒҡйӣҶиө·дҫҶпјҢз№јзәҢзҷјй…өгҖӮжҲ‘зҗҶжғідёӯжҳҜеӣӣеҖӢйҠҖ幕жһ¶еңЁе·Ҙең°еӣӣйҖұпјҢдҪҶеҒҡдёҚеҲ°гҖӮ
иӘӘеҲ°еҪұеғҸиҲҮ當дёӢпјҢжҲ‘еҖ‘зңҹзҡ„еңЁеһғеңҫе Ҷж’ҝеҲ°еЈһжҺүзҡ„е№»зҮҲзүҮпјҢиЈЎйқўжҳҜ70е№ҙд»Јзҷ©з—…йҳІжІ»зҡ„е№»зҮҲзүҮпјҢеҫҲй«’пјҢжңүдәӣи—ҘиҶңеЈһжҺүпјҢдёҚд№ҹжҳҜеҸҰдёҖзЁ®з—…жҜ’пјҹжңүејөе№»зҮҲзүҮпјҢз•«йқўжҳҜеҖӢдәҢеҚҒеҮәй ӯгҖҒеҫҲжјӮдә®зҡ„еҘіз”ҹпјҢеүӣзҷјз—…пјҢжүӢдёҠеҮәзҸҫдёҖдәӣеӮ·з–ӨпјҢдёҖзҫӨдәәеңҚи‘—з ”з©¶пјҢеҘіз”ҹзңӢиө·дҫҶеҝғжғ…еҫҲдёҚеҘҪгҖӮжјўз”ҹз—…жңғзҘһ經з—ӣпјҢжҲ‘еҖ‘еҫһеҝғзҗҶеҲ°з”ҹзҗҶйғҪз„Ўжі•жғіеғҸгҖӮзңӢеҲ°йӮЈејөе№»зҮҲзүҮпјҢжҲ‘йқһеёёйӣЈйҒҺпјҢдҪ еҸҜд»ҘжғіеғҸйҖҷејөз…§зүҮд№ӢеҫҢе°ұжҳҜеҘ№дёҚж–·ең°еҙ©еЎҢпјҢдҪ жңғжғіеғҸеҜҢеӯҗе§Ҡе№ҙиј•еҒҘеә·жҷӮжҳҜд»ҖйәјжЁЎжЁЈпјҹ已經зңӢдёҚеҲ°дәҶгҖӮжҲ‘еҺҹжң¬жғіеңЁеұ•е ҙж”ҫйҖҷдәӣе№»зҮҲзүҮпјҢдҪҶжҲ‘жІ’жңүз”ЁпјҢеӣ зӮәжҲ‘иҰәеҫ—жҲ‘жІ’жңүиіҮж јз”ЁгҖӮ
жҲ‘жғіжҲ‘еҖ‘йғҪжңүиІ¬д»»пјҢеңЁи„«й–ӢйҒӢеӢ•еҫҢеҶҚйҖІиЎҢж•ҳдәӢпјҢе°ұжҳҜж—Ҙеёёз”ҹжҙ»дёӯйҒӢеӢ•зҡ„延зәҢгҖӮжҙӘеёӯиҖ¶пјҲJacques RanciereпјүзӮәдәҶи§Јжұәжі•еңӢ68еӯёйҒӢзҡ„е•ҸйЎҢпјҢиҠұеҚҒе№ҙеңЁеҗ„ең°и’җйӣҶе·ҘдәәжӘ”жЎҲпјҢж„ҹжҖ§еҲҶдә«зҡ„зҗҶи«–д№ҹз”ұйҖҷдәӣж–°иҒһжӘ”жЎҲиҖҢдҫҶгҖӮе°ұеғҸжІҷиЈЎж·ҳйҮ‘пјҢжңҖз©ҚжҘөзҡ„ж„Ҹзҫ©жҳҜе®ғе°ҚеҸғиҲҮиҖ…зҡ„еҪұйҹҝпјҢеҫҲеӨҡе№ҙиј•дәәдёҖй–Ӣе§Ӣеё¶и‘—зҙ жЁёзҡ„дәәйҒ“дё»зҫ©йҖІе…ҘжЁӮз”ҹпјҢдҪҶиЈЎйқўжңүж®ҳй…·зҡ„й¬ҘзҲӯгҖҒдёҚе Әзҡ„з–ҫз—…пјҢйҒӢеӢ•зҡ„иӨҮйӣңиЎқж“Ҡе°Қд»–еҖ‘зҡ„еҪұйҹҝжҳҜд»Җйәјпјҹж•…дәӢжҳҜиҰҒиҮӘе·ұеҺ»еүөйҖ пјҢз„ЎжүҖи¬ӮзңҹеҜҰиҷӣж§ӢпјҢ當йҖҷдәӣеҝғжғ…з”Ёж–Үеӯ—жҲ–е…¶д»–еҪўејҸжӣёеҜ«еҮәдҫҶпјҢе°ұз•ҷдёӢж„ҲеӨҡеҸҜиғҪжҖ§пјҢжӣҝеҫҢйқўзҡ„дәәеүөйҖ жӣҙеӨҡеҸҚзңҒзҡ„ж©ҹжңғпјҢжҲ–еҒ¶з„¶ж’һеҮәе…¶д»–жғіеғҸгҖӮ
жЁӮз”ҹеҰӮжһңеҸӘи®ҠжҲҗдёҖеҖӢеҚҡзү©йӨЁпјҢжӘ”жЎҲ被收еҲ°еңӢ家пјҢйӮЈйәјжЁӮз”ҹйҒӢеӢ•йӮ„жҳҜиў«дё»ж—ӢеҫӢеҢ–гҖӮж”ҝзӯ–е°ҚйҢҜиҲҮеҗҰз•ҷзөҰеӯёиҖ…еҺ»зҲӯиҫҜеҗ§пјҢжңҖз©ҚжҘөзҡ„ж„Ҹзҫ©пјҢжҳҜе®ғе°ҚеҸғиҲҮиҖ…зҡ„еҪұйҹҝгҖӮжӘ”жЎҲзҡ„зӣ®зҡ„жҳҜжІ»зҗҶжҖ§пјӣдҪҶж°‘й–“жӘ”жЎҲгҖҒеңЁйҮҺзҹҘиӯҳжҒ°жҒ°еҸҜд»Ҙи—ҸеҫҲеӨҡжқұиҘҝпјҢдёҚзҹҘйҒ“жңғжҠҳе°„еҮәд»ҖйәјгҖӮе°ұеғҸиҠіз¶әзҡ„ж„ҹжҖ§жӘ”жЎҲпјҢиЈЎйқўзҡ„ж„ҹжғ…жҳҜйқһеёёзңҹеҜҰзҡ„пјҢеҘ№иҺ«еҗҚе…¶еҰҷйҖІе…ҘжЁӮз”ҹйҖҷеҖӢе ҙеҹҹпјҢе°Қз”ҹе‘ҪжңүеҫҲеӨҡеӣ°жғ‘пјҢдҪҶеҘ№е“ӘжңүиғҪеҠӣи§ЈжұәйҖҷдәӣе•ҸйЎҢпјҹеҸӘжңүеҫҲеӨҡе°Қи©ұгҖҒз”ҹе‘ҪжҖқиҖғпјҢиЈЎйқўеҸҜиғҪй–ғзҸҫдёҖеҸҘи©ұи®“дҪ з”ўз”ҹжғіеғҸпјҢдәәз”ҹдёӯжңүеҫҲеӨҡеҒ¶з„¶жҖ§ж’һдҫҶж’һеҺ»пјҢеҰӮжһңеҫһдёӯи®ҖеҲ°дёҖеҸҘжңүж„ҸжҖқзҡ„и©ұд№ҹе°ұеӨ дәҶгҖӮйҖҷжүҚжҳҜи—қиЎ“зҡ„ж„Ҹзҫ©е’ҢиІўзҚ»пјҢжҲ‘иҰәеҫ—иҠіз¶әжүҚжҳҜ當代и—қ術家гҖӮ
е°ҚжҲ‘дҫҶиӘӘпјҢеҪұеғҸе°ұжҳҜиғҪеӢ•жҖ§гҖӮжҲ‘йҖҷйәјжҘӯйӨҳпјҢж•ҳдәӢеҸҲдёҚжё…пјҢж•…дәӢеҸҲдёҚеҘҪзңӢпјҢеҲ°еә•еңЁжӢҚд»ҖйәјпјҹдҪҶз•ўз«ҹд№ҹж··еҲ°зҸҫеңЁпјҢйҖҷдёҚе°ұжҳҜиғҪеӢ•жҖ§зҡ„жңҖеҘҪиӘӘжҳҺе—ҺпјҹжүҖд»ҘжҲ‘дёҚеңЁж„ҸдҪңиҖ…и«–гҖҒдё»жөҒйқһдё»жөҒд№ӢйЎһзҡ„е•ҸйЎҢгҖӮиӢҘе•ҸжҲ‘зӮәдҪ•з”ЁеҪұеғҸпјҢжҳҜеӣ зӮәжҲ‘еёёеёёзңӢеҲ°з•«йқўпјҢжҜ”еҰӮиҚүеҸўдёӯе…©жүҮиў«дёҹжЈ„зҡ„й–ҖпјҢдёӯй–“з©ҝйҒҺеҺ»жңүж №жҹұеӯҗпјҢеҫһйӮЈиЈЎзңӢеҮәеҺ»еҸҜд»ҘзңӢеҲ°зҙҚйӘЁеЎ”гҖӮжҲ‘жӢҚзҡ„жҜҸеҖӢжҷҜпјҢйғҪжңғеңЁйӮЈиЈЎеҫ…еҫҲд№…жҲ–иө°еҫҲеӨҡйҒҚпјҢжҜҸж¬Ўиө°еҲ°йӮЈйӮҠжҲ‘йғҪиҰәеҫ—еҘҪеғҸжңүеҖӢжқұиҘҝпјҢжңүдёҖеӨ©зӘҒ然зңӢеҲ°дёҖеҖӢз•«йқўпјҢжӢҚзҡ„жҷӮеҖҷжҲ‘е°ұжҠҠе…©жүҮй–ҖжӢүиө·дҫҶеӣәе®ҡгҖӮжҲ‘жІ’жңүи¶…иғҪеҠӣпјҢе”ҜдёҖзҡ„иғҪеҠӣе°ұжҳҜиҺ«еҗҚе…¶еҰҷзңӢеҲ°дёҖдәӣжқұиҘҝпјҢ然еҫҢжӢҚеҮәдҫҶпјҢжІ’зңӢеҲ°д№ӢеүҚжҲ‘йғҪдёҚжңғеҺ»еҒҡгҖӮе·ІзҹҘзҡ„дёҚйңҖиҰҒжҲ‘еҖ‘еҒҡпјҢеҪұеғҸдёӯжңүдёҖдәӣиҺ«еҗҚзҡ„дёҚзҹҘдҪ•зү©пјҢйҖҷжүҚжҳҜжҲ‘иҰҒжӢҚзҡ„гҖӮи—қиЎ“зҡ„дҪңз”Ёе°ұжҳҜеҸҜд»Ҙе–ҡиө·еҗ„зЁ®жғіеғҸпјҢжңүжҷӮжІ’д»Җйәјй ӯз·’пјҢжңүд№ҹжҳҜд№ӢеҫҢеҶҚж•ҙзҗҶгҖӮзҫҺеӯёзҡ„еҺҹж„ҸжҳҜж„ҹжҖ§иЎЁйҒ”зҡ„еҹәзӨҺпјҢиҖҢеҸҚзҫҺеӯёзңҹжӯЈзҡ„ж„Ҹзҫ©еңЁж–јж•ҳдәӢж°ёйҒ дёҚеӨ пјҢйӮЈиЈЎйқўжңғжңүеҸҰеӨ–зҡ„еӢ•иғҪгҖӮ
еӣһеҲ°ж”ҫжҳ зҸҫе ҙзҡ„е•ҸйЎҢпјҢзҸҫе ҙд№ӢжүҖд»ҘеҘҪзңӢпјҢдёҚжҳҜеӣ зӮәйӮЈзЁ®дәәйЎһеӯёејҸзҡ„гҖҒеҖ«зҗҶж„Ҹзҫ©дёҠзҡ„иҰҒеӣһеҲ°зҸҫе ҙж”ҫзөҰжӢҚж”қе°ҚиұЎзңӢгҖӮжҲ‘еҺҹе§Ӣзҡ„иЁӯжғійғҪжҳҜеҰӮдҪ•еңЁзҸҫе ҙж”ҫзүҮпјҢи§ҖзңҫзңӢеҲ°зҡ„еҸӘжҳҜзүҮж®өпјҢжҜҸеҖӢдәәиӘӘеҮәзҡ„е…§е®№дёҚдёҖжЁЈпјҢжҜҸеҖӢдәәйғҪжңүиҮӘе·ұзҡ„ж„ҹжҖ§пјҢжҲ‘зҗҶжғідёӯзҡ„е°ұжҳҜйҡЁдҫҝзңӢзңӢпјҢиҮӘз”ұйҒҠиө°пјҢжқұжҷғиҘҝжҷғпјҢжӢјж№ҠеҮәдёҖйғЁиҮӘе·ұзҡ„и’ҷеӨӘеҘҮгҖӮ
жүҖд»ҘжҲ‘ж°ёйҒ йғҪеңЁжӢҚйҒҺе ҙжҲІпјҢжІ’жңүдёү幕еҠҮзҹӣзӣҫгҖҒиЎқзӘҒгҖҒи§ЈжұәпјҢеҸӘжҳҜеҫһдёҖеҖӢе ҙжҷҜйҒҺе ҙеҲ°еҸҰдёҖеҖӢгҖӮеё•зҙўйҮҢе°јпјҲPier Paolo PasoliniпјүиӘӘгҖҢдәәз”ҹе°ұжҳҜдёҖеҖӢй•·йҸЎй ӯгҖҚпјҢе…¶еҜҰдәәз”ҹд№ҹжҳҜдёҖеҖӢиӨҮйӣңзҡ„и’ҷеӨӘеҘҮпјҢжҲ‘еҖ‘дёҚзҹҘйҒ“иө°еҮәеҺ»жҺҘдёӢдҫҶжңғзў°еҲ°иӘ°гҖҒи«Үд»ҖйәјпјҢжҲ–жҳҜжЁ“дёӢзҸҫеңЁжӯЈзҷјз”ҹд»ҖйәјдәӢгҖӮжҲ‘еҖ‘дёҚд№ҹйғҪеңЁйҒҺе ҙе—ҺпјҹжҲ‘е°ҚеҫҲеӨҡйӣ»еҪұеҸӘиЁҳеҫ—зүҮж®өпјҢдҪҶеҸӘиҰҒиЈЎйқўиӘӘдёҚеҮәзӮәд»Җйәјзҡ„еҚҒеҲҶйҗҳе°ҚжҲ‘жңүе•ҹзҷје°ұеӨ дәҶгҖӮиӘһиЁҖиҖ—зӣЎд№ӢжҷӮпјҢе°ұжҳҜи—қиЎ“еӯҳеңЁзҡ„ең°ж–№гҖӮ
з·ЁиҖ…иЁ»пјҡ
1 й—ңж–јзҙҖйҢ„зүҮгҖҠи”Јжёӯж°ҙ—еҸ°зҒЈеӨ§зңҫ葬葬е„ҖгҖӢиҲҮиҫҜеЈ«зӣ§дёҷдёҒпјҢж„ҹи¬қйҷіз•Ңд»ҒиҖҒеё«жҸҗдҫӣжј”и¬ӣзЁҝж•ҙзҗҶж–Үеӯ—дәҲзӯҶиҖ…еҸғиҖғгҖӮең–зүҮз”ұйҷіз•Ңд»ҒжҸҗдҫӣпјҢж”ҫжҳ зҸҫе ҙз…§зүҮз”ұйҷіеҸҲз¶ӯж”қеҪұгҖӮиҖҢй—ңж–ји”Јжёӯж°ҙзҡ„гҖҢеӨ§зңҫ葬гҖҚпјҢд№ғи”Јжёӯж°ҙеҖӢдәәзҡ„еә¶ж°‘й«”еҲ¶еӨ§еһӢ葬зҰ®пјҢзӣӣжіҒз©әеүҚпјҢ1931е№ҙ8жңҲ23ж—Ҙз”ұж°ёжЁӮеә§й–Ӣе§Ӣз№һиЎҢпјҢдёӯеӨ®жңүи”Јжёӯж°ҙе…Ҳз”ҹйҒәеғҸпјҢе…©ж—ҒжңүгҖҢзІҫзҘһдёҚжӯ»гҖҚгҖҒгҖҢйҒәиЁ“зҢ¶еңЁгҖҚгҖҒгҖҢеӨ§зңҫе№ІеҹҺгҖҚгҖҒгҖҢи§Јж”ҫй¬Ҙе°ҮгҖҚжЁҷиӘһпјҢжӯҰиЈқиӯҰеҜҹеҡҙеҠ жҲ’еӮҷпјҢе…¶жүҖеҮқиҒҡзҡ„еј·еӨ§иғҪйҮҸгҖҢеҡҮз ҙжҙ»зёҪзқЈгҖҚгҖӮпјҲдҫҶжәҗпјҡWikipediaпјү
2 гҖҠж®ҳйҹҝдё–з•ҢгҖӢз”ұеӣӣй »йҒ“йҢ„еғҸзө„жҲҗпјҢеҲҶеҲҘзӮәпјҡгҖҠд№ӢеҫҢиҲҮд№ӢеүҚгҖӢгҖҒгҖҠйҷӘдјҙж•ЈиЁҳгҖӢгҖҒгҖҠзЁ®жЁ№зҡ„дәәгҖӢгҖҒгҖҠиў«жҮёзҪ®зҡ„жҲҝй–“гҖӢгҖӮ
3 DDSзӮәжҲҙжҷ®жқҫпјҲDapsoneпјүзҡ„иӢұж–Үз°ЎзЁұпјҢ1950е№ҙ代經иҫІеҫ©жңғеј•йҖІпјҢеӣ дёҚзҹҘеҰӮдҪ•дҪҝз”ЁеҠ‘йҮҸпјҢйҷўж°‘被當жҲҗеҜҰй©—е“ҒпјҢйҒҺйҮҸе°ҺиҮҙеҡҙйҮҚз—ІзҳӢеҸҚжҮүеҸҠиІ§иЎҖпјҢеүҜдҪңз”ЁеҢ…жӢ¬зҙ…иЎҖзҗғз ҙеЈһгҖҒиЎҖз®ЎзҲҶиЈӮгҖҒзҘһ經з—ӣеҠ еҠҮзӯүпјҢйҖ жҲҗйҷўж°‘дёҚе Әз–јз—ӣжҠҳзЈЁеӨ§йҮҸиҮӘж®әгҖӮ
4 ејөиҠіз¶әзӮәгҖҠйҷӘдјҙж•ЈиЁҳгҖӢдёӯзҡ„дё»и§’пјҢд№ҹжҳҜгҖҠе№ёзҰҸеӨ§е»ҲIгҖӢдёӯж•ҙзҗҶжјўз”ҹз—…жӮЈдәЎиҖ…еҗҚеҶҠиҖ…дёҖи§’гҖӮ
5 еңЁгҖҠиў«жҮёзҪ®зҡ„жҲҝй–“гҖӢдёӯпјҢйҷёй…ҚжүҖе”ұзҡ„жҳҜ1940е№ҙд»ЈжҠ—ж—ҘжҲ°зҲӯжң«жңҹпјҢдёӯеңӢе…ұз”ўй»Ёж–ји§Јж”ҫеҚҖиЈҪдҪңзҡ„ж–Үи—қйӣ»еҪұгҖҠзҷҪжҜӣеҘігҖӢдёӯзҡ„жӯҢжӣІгҖҲеҢ—йўЁеҗ№гҖүгҖӮ
пјҲжң¬ж–ҮзҜҖйҢ„зүҲжң¬еҗҢжӯҘеҲҠзҷ»ж–јгҖҠд»Ҡи—қиЎ“гҖӢйӣңиӘҢдәҢжңҲиҷҹпј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