в– ж–Үз« дё»ең–пјҡгҖҠиҝӘе…ӢжЈ®и©Ұй©—жңүиҒІйӣ»еҪұгҖӢпјҢжҳҜзҸҫеӯҳжңҖж—©зҡ„жңүиҒІйӣ»еҪұиіҮж–ҷпјҢжң¬зүҮж”қж–ј1894е№ҙеә•жҲ–1985е№ҙеҲқпјҢеңЁж„ӣиҝӘз”ҹзҙҗжҫӨиҘҝе·ҘдҪңе®ӨжӢҚж”қпјҢжҳҜе…¶е“Ўе·ҘиҝӘе…ӢжЈ®зӮәдәҶж„ӣиҝӘз”ҹз ”зҷјзҡ„йқһеҗҢжӯҘжңүиҒІйӣ»еҪұж”ҫжҳ ж©ҹгҖҢжңүиҒІжҙ»еӢ•йӣ»еҪұж©ҹгҖҚ пјҲKinetophoneпјүжӢҚж”қзҡ„и©Ұй©—е“ҒгҖӮ
пјҲеҠҮз…§зҝ»жӢҚиҮӘYoutubeпјү
|
第еҚҒд№қеұҶеҸ°еҢ—йӣ»еҪұзҜҖе°ҮеҫһйҹіжЁӮеҮәзҷјпјҢзӮәеҪұиҝ·еҖ‘её¶дҫҶе…Ёж–°зҡ„иҰ–иҒҪ經驗гҖӮдёҚеғ…и«ӢдҫҶйӣ·е…үеӨҸеүөдҪңдё»йЎҢж—ӢеҫӢпјҢе…¬дҪҲзҡ„йҰ–жіўзүҮе–®жӣҙжҳҜжҺЁеҮәгҖҢиҒҪиҰӢйӣ»еҪұзҡ„еҝғи·іпјҡжһ—еј·гҖҚе–®е…ғпјҢж”ҫжҳ з”ұжһ—еј·й…ҚжЁӮзҡ„е…ӯйғЁйӣ»еҪұпјҢеҢ…жӢ¬гҖҠеҚ—еңӢеҶҚиҰӢпјҢеҚ—еңӢгҖӢгҖҒгҖҠеҚғзҰ§жӣјжіўгҖӢгҖҒгҖҠдё–з•ҢгҖӢгҖҒгҖҠеӨ©жіЁе®ҡгҖӢгҖҒгҖҠз„Ўз”ЁгҖӢиҲҮгҖҠеҲәе®ўиҒ¶йҡұеЁҳгҖӢпјҢйҖҸйҒҺиҒІйҹіи®“еӨ§е®¶йҮҚж–°ж„ҹеҸ—дҫҜеӯқиіўиҲҮиіҲжЁҹжҹҜзҡ„еӨ§её«дҪңе“ҒпјҢеҸҰеӨ–пјҢйҰ–еәҰй–Ӣж”ҫй…ҚжЁӮзҸҫе ҙпјҢйӮҖи«Ӣи§ҖзңҫиҲҮжһ—еј·дёҖиө·йҖІе…ҘзҺ„еҰҷзҡ„еүөдҪңзӢҖж…ӢгҖӮеңЁзңҫдәәеӮҫиҖіжңҹзӣјзҡ„еҗҢжҷӮпјҢж”ҫжҳ йҖұе ұжҺЁеҮәгҖҗж”ҫжҳ иҒІйҹігҖ‘зі»еҲ—ж–Үз« дҫҶиҒҠиҒҠйӣ»еҪұиҒІйҹіпјҢжә–еӮҷиҝҺжҺҘд»Ҡе№ҙеӨҸеӨ©жһ—еј·йңҮж’јзҡ„йҹіеғҸдё–з•ҢгҖӮ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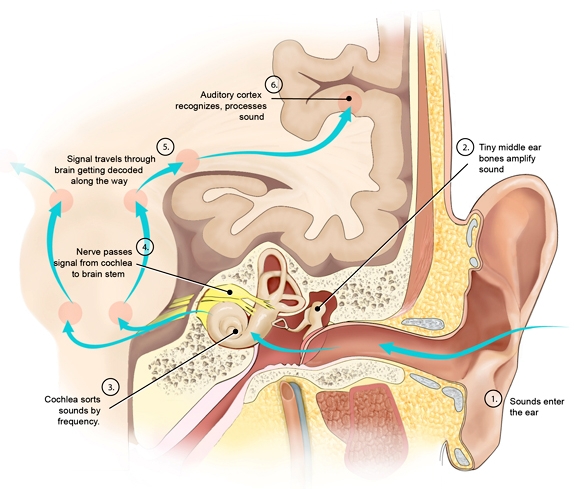
в–ҚгҖҢеҜ§йқңгҖҚеҚ»еҸҲгҖҢдёҚеҜ§йқңгҖҚзҡ„ж„ҹе®ҳйқ©е‘Ҫ
жҲ‘еҖ‘зҡ„иҖіжңөйҡЁжҷӮйҡЁең°йғҪеңЁжҺҘ收周йҒӯзҡ„иЁҠжҒҜпјҢдҪҶеӨ§еӨҡж•ёзҡ„жҷӮй–“иЈЎеҚ»дёҚиҮӘиҰәпјҢеӣ зӮәеңЁиҰ–иҰәдё»е°Һзҡ„иӘҚзҹҘзі»зөұиЈЎпјҢдәәеҖ‘зёҪжҳҜдҫқйқ зңјзқӣдҫҶиӘҚиӯҳдё–з•ҢпјҢиҖҢеҝҪз•ҘдәҶиҮӘе·ұжүҖиә«иҷ•зҡ„зү©иіӘз’°еўғпјҢе…¶еҜҰиәҚеӢ•и‘—еҗ„зЁ®иҒІйҹҝгҖӮйҡЁи‘—科жҠҖзҡ„зҷјеұ•пјҢжҠҠе°ҚиҒІйҹізҡ„ж„ҹеҸ—еҫһиҰ–иҰәзӮәе°Ҡзҡ„ж„ҹе®ҳй«”еҲ¶иЈЎйҮӢж”ҫеҮәдҫҶпјҢйҖҸйҒҺдёҚеҗҢзҡ„еӘ’й«”пјҢжҲ‘еҖ‘зөӮж–јжү“й–ӢдәҶиҖіжңөпјҢйҮҚж–°еӯёзҝ’иҒҶиҒҪгҖҒеӯёзҝ’ж„ҹеҸ—пјҢеңЁдёҖжҲҗдёҚи®Ҡзҡ„ж—Ҙеёёз”ҹжҙ»иЈЎпјҢзҷјзҸҫе……ж»ҝзҜҖеҘҸзҡ„иҒІйҹійўЁжҷҜгҖӮйҡЁи‘—иҒІйҹіиӨҮиЈҪ科жҠҖжІҝйқ©пјҢеҫһз•ҷиҒІж©ҹгҖҒ收йҹіж©ҹгҖҒе”ұж©ҹгҖҒйҢ„йҹіж©ҹгҖҒWalkmanгҖҒIPodпјҢеҫһеҜҰй«”и®ҠжҲҗж•ёдҪҚпјҢеҫһйЎһжҜ”еҲ°дёІжөҒзҡ„жҷӮд»ЈпјҢйҡЁи‘—йҢ„иЈҪгҖҒеҶҚиЈҪгҖҒж“ҙеӨ§гҖҒж’ӯж”ҫгҖҒиЈқијүиҒІйҹіе…§е®№зҡ„еҪўй«”дёҚж–·ж”№и®ҠпјҢйҖҷдәӣиҒІйҹҝд№ҹйҖҸйҒҺеҗ„зЁ®дёҚеҗҢеҪўејҸпјҢйқ©ж–°жҲ‘еҖ‘зҡ„иҒҪиҰәж„ҹзҹҘгҖӮ
|
в–Қ延伸й–ұи®Җ
597жңҹгҖҗж”ҫжҳ й ӯжўқгҖ‘
е°ҲиЁӘеҸ°еҢ—йӣ»еҪұзҜҖзёҪзӣЈжІҲеҸҜе°ҡгҖҒзӯ–еұ•дәәйғӯж•Ҹе®№пјҡгҖҢеҪұеұ•жҳҜдёҖзЁ®жҠ•зҹіе•Ҹи·Ҝзҡ„йҒҺзЁӢгҖҚ
|
иҒІйҹійЈ„еҝҪзҡ„ж•Јж’ӯжҖ§пјҢеҫ—д»ҘеҢ–зӮәз„ЎеҪўгҖҒз©ҝи¶Ҡз•ҢйҷҗпјҢйҖҷжЁЈзҡ„еӘ’жқҗзү№жҖ§еңЁиҒІйҹіеүөдҪңиҲҮж’ӯж”ҫжҠҖиЎ“зҡ„зҷјеұ•йҒҺзЁӢдёӯпјҢиЎқж“ҠиҲҠжңүзӨҫжңғйҡҺзҙҡеҠғеҲҶдёӢе°ҚеӮізөұи—қиЎ“ж¬Јиіһзҡ„иҰҸиЁ“пјҢжҢ‘жҲ°е°ҲеҝғиҒҶиҒҪиҲҮе…ЁзҘһиІ«жіЁжүҚиғҪй ҳжңғзҡ„еҜ©зҫҺзҙ йӨҠгҖӮеҚҒд№қдё–зҙҖжӯҗжҙІгҖҢеёғзҲҫе–¬дәһгҖҚйҡҺзҙҡе°Қж–јйҹіжЁӮж¬Јиіһзҷјеұ•еҮәдёҖеҘ—жІҝз”ЁиҮід»Ҡзҡ„еҡҙиӮ…иҒҶиҒҪе„ҖејҸпјҢи§Җзңҫеҝ…й ҲеңЁеӨ§еһӢйҹіжЁӮе»іиЈЎжӯЈиҘҹеҚұеқҗпјҢзҷјеҮәдёҖй»һиҒІйҹійғҪжңғеј•дҫҶеҒҙзӣ®пјҢйҖЈйј“жҺҢзҡ„жҷӮж©ҹдёҚе°ҚйғҪжңғиў«иҰ–зӮәжңүеӨұж•ҷйӨҠгҖӮдҪҶ當ж„ӣиҝӘз”ҹзҷјжҳҺзҡ„з•ҷиҒІж©ҹзҷјеҮәеҘҮеҰҷиҒІйҹҝпјҢзҫӨзңҫи¶Ёд№ӢиӢҘ鶩пјҢжҳҜе…¬й–Ӣж…¶е…ёжҲ–еӨ§еһӢжҙ»еӢ•дёҚеҸҜзјәе°‘зҡ„ж„ҹе®ҳдә«еҸ—пјҢи·іи„«еӮізөұзҡ„иҒҶиҒҪж–№ејҸпјҢж–°зҡ„еӨ§зңҫдј‘й–’еЁӣжЁӮж–јжҳҜиӘ•з”ҹгҖӮ
йӣ–然еӮіж’ӯиӨҮиЈҪ科жҠҖжғ№жғұдәҶдёҚе°‘зӣёдҝЎи—қиЎ“жҳҜзҚЁдёҖз„ЎдәҢзҡ„дәәпјҢеғҸжҳҜеңЁ1920е№ҙд»Јзҡ„зҫҺеңӢпјҢ收йҹіж©ҹйҺ®ж—Ҙж’ӯж”ҫзҡ„ж–°иҒһзҜҖзӣ®гҖҒжј”и¬ӣгҖҒжөҒиЎҢйҹіжЁӮгҖҒе»Јж’ӯеҠҮпјҢжҲҗзӮәж—Ҙеёёз”ҹжҙ»иЈЎзҡ„иғҢжҷҜиҒІйҹҝпјҢдјҙйҡЁи‘—дәәеҖ‘е·ҘдҪңгҖҒи®ҖжӣёгҖҒеҒҡ家дәӢзӯүзҡ„йҖҷ種收иҒҪзҝ’慣儼然еҪўжҲҗдёҖзЁ®еӨ§зңҫж–ҮеҢ–пјҢйҖҷдҪҝдәәж„ҹеҲ°жҶӮеҝғпјҢд»–еҖ‘е°ҮйҖҷдәӣдёҚж–·ж”ҫйҖҒзҡ„иҒІйҹҝиҰ–зӮәеҷӘйҹіпјҢиӘҚзӮәе®ғеҖ‘жңғз ҙеЈһйӮЈдәӣйңҖиҰҒеҝғзҘһе®үеҜ§иҲҮе°ҲеҝғиҮҙеҠӣе·ҘдҪңзҡ„дәәгҖӮ
иҖҢж’ӯж”ҫжҠҖиЎ“зҡ„жј”йҖІпјҢи®“иҒҶиҒҪдёҚеҶҚеҸӘжҳҜеӣәе®ҡеңЁйҹіжЁӮе»ізҡ„йӣҶй«”жҙ»еӢ•пјҢе®ғдёҚж–·жҢҒзәҢи‘—е®ғзҡ„гҖҢеҜ§йқңпјҸдёҚеҜ§йқңгҖҚйқ©е‘ҪпјҢж”№и®ҠжҲ‘еҖ‘е°ҚзҸҫеҜҰи®ҠеҢ–зҡ„ж„ҹеҸ—пјҢд№ҹйҮҚж–°еҪўеЎ‘дәҶзү№жңүзҡ„иҮӘжҲ‘иЎЁйҒ”ж–№ејҸгҖӮеҰӮйҡЁиә«иҒҪзҡ„еҮәзҸҫпјҢеҸӘиҰҒеё¶дёҠиҖіж©ҹпјҢе°ұиғҪйҖІе…ҘзҚЁз«Ӣзҡ„иҒҶиҒҪз©әй–“пјҢзһ¬й–“и®“жІҲжӮ¶з„Ўе‘ізҡ„зҸҫеҜҰз’°еўғпјҢйҡЁи‘—иҒІйҹіжөҒиҪүиҖҢи®Ҡеҫ—зҫҺеҘҪпјҢдёҚи«–жҳҜеңЁж“Ғж“ зҡ„и»Ҡе»ӮгҖҒзӯүеҫ…зҡ„йҡҠдјҚпјҢжҲ–жҳҜйҮҚиӨҮйҒӢиҪүзҡ„и·‘жӯҘж©ҹдёҠпјҢдёҚз®ЎжҳҜд»ӨдәәжҢҜеҘ®зҡ„зҜҖеҘҸпјҢжҲ–жҳҜжІҲжөёеӨўе№»зҡ„ж—ӢеҫӢпјҢйғҪйҖҸйҒҺиҒҶиҒҪеүөйҖ иҮӘжҲ‘иҲҮдё–з•Ң嶄新зҡ„дә’еӢ•ж–№ејҸгҖӮ
дҪҶдёҖйҖІе…Ҙйӣ»еҪұйҷўиЈЎпјҢйҖҷиҒІеӢўжө©еӨ§зҡ„科жҠҖж„ҹзҹҘйқ©е‘ҪеҚ»з„Ўжі•и§Јж”ҫж—©е·ІйҖІеҢ–зҡ„иҒҪиҰәпјҢд»Қ然無法йҒҝе…Қең°дҫ·йҷҗж–јиҰ–иҰәжқҹзёӣзҡ„гҖҢи§ҖеҪұгҖҚ經驗裡гҖӮеҸҰеӨ–пјҢз”ұжӯӨиЎҚз”ҹеҘҪиҗҠеЎўз„ЎжҺҘзё«з·ҡжҖ§ж•ҳдәӢзҡ„еүӘжҺҘжҰӮеҝөиЈЎпјҢйҢ„йҹійҒҺзЁӢзҡ„йӣңйҹіиҲҮеҗ„зЁ®еҪұйҹҝе°ҚзҷҪжё…жҷ°зҡ„еӣ зҙ йғҪиҰҒиў«ж¶ҲйҷӨгҖӮеңЁжӯӨиҰҸзҜ„дёӢпјҢйӣ»еҪұеүөйҖ йҹіз•«еҗҲдёҖзҡ„е®ҢзҫҺзңҹеҜҰж„ҹеҸ—пјҢи®“дәәеҸҜд»Ҙе®Ңе…ЁжҠ•е…ҘеңЁеҠҮжғ…иЈЎпјҢиҖҢзөІжҜ«дёҚеҜҹиҰәиЈҪдҪңзҡ„з—•и·ЎгҖӮ

в–ҚзңјзқӣзңӢдёҚеҲ°зҡ„пјҢжІ’жңүеҗҚеӯ—зҡ„йӣ»еҪұе…ғзҙ
д№ҹиЁұжӯЈеӣ еҰӮжӯӨпјҢйӣ»еҪұиЈЎзҡ„иҒІйҹіиҲҮиҒҪиҰәж„ҹеҸ—жүҚеҫҲе°‘иў«и«Үи«–пјҢеӣ зӮәд№ҹиЁұдёҖж—Ұи§ҖзңҫзҷјзҸҫиҒІйҹізҡ„еӯҳеңЁпјҢе°ұз ҙеЈһдәҶиҷӣж§ӢзңҹеҜҰзҡ„е®ҢзҫҺз„ЎжҡҮгҖӮеңЁжҲ‘еҖ‘и«Үи«–йӣ»еҪұзҡ„ж—ҘеёёиӘһиЁҖйғҪе°Һеҗ‘и§ҖзңӢпјҢиҖҢйқһиҒҶиҒҪпјҢжҲ‘еҖ‘жңғиӘӘпјҡгҖҢиҒҪе»Јж’ӯгҖҒиҒҪе”ұзүҮгҖҒиҒҪI-PodгҖҚдҪҶдёҚжңғиӘӘпјҡгҖҢиҒҪдёҖе ҙйӣ»еҪұгҖҚгҖӮеҫһиӢұж–ҮдҫҶзңӢе°Өе…¶жҳҺйЎҜпјҢе…¶дёӯеӨ§йҮҸзҡ„иҰ–иҰәиЎҚз”ҹз”Ёеӯ—пјҢдҫӢеҰӮгҖҢжҲ‘жҮӮгҖҚжҳҜI seeпјҢгҖҢеӣһйЎ§гҖҚжҳҜreviewпјҢеҸҰеӨ–йӮ„жңүгҖҢиҒҡз„ҰгҖҚfocusпјҢгҖҢдё»и§ҖиҰ–й»һгҖҚpoint of viewпјҢи·ҹгҖҢеҮқиҰ–гҖҚgazeзӯүзӯүпјҢйҖҷдәӣеёёиҰӢзҡ„йӣ»еҪұеҲҶжһҗз”ЁиӘһиЈЎжҳҺйЎҜеҒҸеҘҪиҰ–иҰәпјҢиҖҢе°Ҳй–ҖжҸҸиҝ°иҒІйҹіиҲҮиҒҪиҰәзҡ„еӯ—еҪҷеҚ»йқһеёёжңүйҷҗпјҢжңүзҡ„д№ҹжҳҜеҫһеҫҢдҫҶзҷјеұ•еҮәдҫҶиҲҮиҰ–иҰәзӣёжҮүзҡ„и©һеҪҷпјҢеҰӮгҖҢдё»и§ҖиҒҪй»һгҖҚпјҲpoint of auditionпјүгҖӮ
в–ҚиҒІйҹіпјҢеҫһжңӘзјәеёӯ
еҚідҪҝйӣ»еҪұиҒІйҹіжҳҜй•·жңҹеҸ—еҝҪз•Ҙзҡ„еӘ’д»ӢпјҢ然иҖҢеңЁйӣ»еҪұзҷјеұ•зҡ„йҒҺзЁӢдёӯеҚ»еҫһдҫҶжІ’жңүзјәеёӯйҒҺгҖӮгҖҢй»ҳзүҮеҫһдҫҶдёҚжҳҜз„ЎиҒІзҡ„гҖҚжҳҜжҲ‘еҖ‘иҖізҶҹиғҪи©ізҡ„и«–иӘҝпјҢдҪҶе…¶еҜҰжӣҙж—©д№ӢеүҚпјҢ當йӣ»еҪұйӮ„дёҚжҲ‘еҖ‘д»ҠеӨ©иӘҚиӯҳзҡ„йӣ»еҪұеҪўејҸжҷӮпјҢе°ұжҳҜиҒІиүІдҝұеӮҷзҡ„еӘ’й«”пјҢйҖҡеёёжІ’жңүеӣәе®ҡж”ҫжҳ зҡ„ең°ж–№пјҢиҖҢжҳҜеңЁйҒҠжЁӮе ҙгҖҒдё»йЎҢйҒҠжЁӮең’гҖҒйҰ¬жҲІеңҳзӯүдј‘й–’еЁӣжЁӮе ҙжүҖпјҢж—©жңҹйӣ»еҪұеҸҜд»ҘиӘӘжҳҜз¶ңеҗҲйӣңиҖҚжӯҢиҲһгҖҒйӯ”иЎ“иЎЁжј”гҖҒе№»зҮҲзүҮиҲҮйӢјзҗҙжј”еҘҸпјҢиһҚеҗҲиҮӘеӢ•жЁӮеҷЁжј”еҘҸзҡ„иұӘиҸҜгҖҢеҪұйҹіз¶ңи—қз§ҖгҖҚгҖӮеҗёеј•и§Җзңҫзҡ„дёҰдёҚжҳҜж•…дәӢпјҢеӣ зӮәеӨҡеҚҠжҳҜд»ӨдәәзңјиҠұз№ҡдәӮжӯҢиҲһиЎЁжј”пјҢжҲ–жҳҜзһ¬й–“зҡ„й©ҡеҘҮпјҢеӣ жӯӨжҳҜеӘ’д»Ӣжң¬иә«еұ•зӨәеҘҮи§Җдё–з•ҢгҖӮ

дёҚйҒҺпјҢиҰ–иҰәж–ҮеҢ–дё»е°ҺжҲ‘еҖ‘е°Қйӣ»еҪұзҡ„иӘҚиӯҳпјҢеӣ жӯӨиҒІйҹіиҲҮиҒҪиҰәж–ҮеҢ–зҡ„ең°дҪҚе§ӢзөӮжҳҜж¬ЎиҰҒзҡ„пјҢйӮ„жңүеҸҰдёҖеҖӢйҮҚиҰҒзҡ„еӣ зҙ жҳҜеңЁеҘҪиҗҠеЎўе·ҘжҘӯзҡ„й«”еҲ¶еҢ–пјҢе»әз«Ӣз·ҡжҖ§еүӘжҺҘеҺҹеүҮд№ӢеҫҢпјҢи®“и§Җзңҫе°ҲжіЁеңЁжғ…зҜҖзҷјеұ•пјҢйӣ»еҪұжҲҗдәҶиӘӘж•…дәӢзҡ„еӘ’д»ӢгҖӮиҖҢеҺҹжң¬иҝ·дәәзҡ„еҗ„зЁ®иҒІйҹҝпјҢйғҪйҖҖзӮәж•ҳдәӢзҡ„иј”еҠ©пјҢдёҰдё”дҫқз…§е°Қж•ҳдәӢжҲ–з•«йқўе№«еҠ©зҡ„йҮҚиҰҒзЁӢеәҰдҫқж¬ЎеҚҖйҡ”жҺ’еәҸзӮәе°ҚзҷҪгҖҒйҹіжЁӮгҖҒй…ҚжЁӮгҖҒйҹіж•ҲиҲҮз’°еўғйҹігҖӮ
жңүиҒІйӣ»еҪұзҡ„еҲқе§ӢпјҢе°ҡжңӘе»әз«Ӣе°ҚзҷҪжё…жҷ°иҲҮйҷҚдҪҺеҷӘйҹізӯүиҒІйҹіеҜ«еҜҰеҺҹеүҮпјҢеүөдҪңиҖ…еҸ–жқҗеҗ„зЁ®еӘ’й«”иҒІйҹҝпјҢз”ўеҮәеҚҒеҲҶе…·жңүеҜҰй©—жҖ§еҸҲеҜҢжңүжҙ»еҠӣзҡ„иҒІйҹіеүөдҪңпјҢ當жҷӮпјҢеғҸжҳҜжі•еңӢе°Һжј”йӣ·е°је…ӢиҗҠзҲҫпјҲRene Claireпјүзҡ„ж—©жңҹжңүиҒІзүҮгҖҠзҷҫиҗ¬жі•йғҺгҖӢ(Le Million, 1931)дҪҝз”ЁиҒІз•«йҢҜдҪҚиЈҪйҖ е–ңеҠҮж•ҲжһңпјҢеұ•зҸҫж··йҹізҡ„еүөж„ҸпјҢеҸ°дёҠжҳҜз”·й«ҳйҹізҡ„жј”е”ұпјҢеҫҢеҸ°дёҖзҫӨиҝҪи‘—еҪ©еҲёзҡ„дәәпјҢй…ҚдёҠеҗөйӣңзҡ„зҗғиіҪиҪүж’ӯиҒІпјҢзңӢдјјз„Ўй—ңиҒҜпјҢеҚ»е·§еҰҷең°еҗ»еҗҲйӣ»еҪұи«·еҲәзӮәиІЎеҜҢ競иіҪзҡ„иҚ’謬еҸҜ笑пјҢд»–е°Қеҗөйӣңз’°еўғйҹізҡ„еүөж„ҸдҪҝз”ЁпјҢдёҰдёҚз”Ёж–ји©®йҮӢеҪұеғҸпјҢиҖҢжҳҜиЎЁзҸҫе…¶з’°еўғзҡ„зү©иіӘзү№жҖ§пјҢдёҚи®“и§Җзңҫйҷ·е…Ҙе°ҚзҷҪе°Һеҗ‘зҡ„жҲІеҠҮеҪўејҸпјҢиҒІйҹізҡ„жң¬иә«дҫҝжҳҜж„Ҹзҫ©зҡ„еӮійҒ”гҖӮ
дёҚйҒҺз’°еўғйҹіеңЁйӣ»еҪұиҒІйҹіиЈЎжҳҜжңҖд№Ҹдәәе•ҸжҙҘзҡ„пјҢе®ғдёҚеғҸйҹіжЁӮйӮЈйәје®№жҳ“еҗёеј•дәәзҡ„жіЁж„ҸпјҢдҪҶе®ғиҒҪиҖҢдёҚиҰӢзҡ„зү№жҖ§пјҢи®“иҹ„дјҸж–јз’°еўғиЈЎзҡ„иҒІйҹҝжҺҷи„«иҰ–еғҸжқҹзёӣпјҢиіҰдәҲзү©иіӘзҸҫеҜҰж–°зҡ„ж„Ҹзҫ©гҖӮеңЁзҸҫеҜҰз”ҹжҙ»иЈЎпјҢйҷӨйқһжҲ‘еҖ‘иғҪеңЁзңҹз©әз’°еўғиЈЎе‘јеҗёпјҢеҗҰеүҮдёҚеҸҜиғҪж„ҹеҸ—全然無иҒІпјҢеҚідҪҝжҳҜеңЁеҜӮйқңзҡ„ж·ұеӨңпјҢд№ҹжңғжңүйҡұи—ҸеңЁй»‘жҡ—еҖӢи§’иҗҪзҡ„иҒІйҹіеңЁи ўи ўж¬ІеӢ•гҖӮеӣ жӯӨйӣ»еҪұз’°еўғйҹізҡ„еүөдҪңиғҪе–ҡйҶ’жҲ‘еҖ‘е°Қж—Ҙеёёз”ҹжҙ»иЈЎйҹіжЁӮжҖ§зҡ„жіЁж„ҸпјҢж„ҹеҸ—е‘ЁйҒӯз’°еўғдёҚж–·жөҒеӢ•зҡ„зҜҖеҘҸиҲҮж—ӢеҫӢпјҢеғҸжҳҜжңҖиҝ‘еёӯжҚІеҪұеЈҮпјҢеҗ‘еҘҪиҗҠеЎўжӯҢиҲһзүҮиҮҙ敬зҡ„гҖҠжЁӮдҫҶи¶Ҡж„ӣдҪ гҖӢпјҲLalalandпјүпјҢдёҖй–Ӣе ҙе°ұжҠҠи§Җзңҫеё¶еӣһеҲ°йӣ»еҪұеүӣй–Ӣе§ӢиӘӘи©ұзҡ„жҷӮд»ЈпјҢзІҫзҙ°еҠ е·Ҙзҡ„з’°еўғйҹіе»әз«ӢиҒҪиҰәдё–з•ҢпјҢи®“ж—Ҙеёёз”ҹжҙ»иЈЎеҫһдёҚиў«жіЁж„Ҹзҡ„еҗ„зЁ®иҒІйҹій “жҷӮи®Ҡеҫ—ж–°й®®жңүи¶ЈгҖӮ

жҙӣжқүзЈҜзҶҷж”ҳзҡ„е…¬и·ҜдёҠе……ж»ҝдәҶе–ҮеҸӯиҒІгҖҒеј•ж“ҺиҒІпјҢе°Һжј”йҒ”зұіжҒ©жҹҘжҫӨйӣ·пјҲDamien ChazelleпјүеҲ©з”Ёеҗ„зЁ®з’°еўғйҹіе»әж§Ӣе…¬и·Ҝзҡ„еҘҮеҰҷйҹіжҷҜпјҢжӣҙжңүи¶Јзҡ„жҳҜпјҢи§ҖзңҫиҒҪиҰӢжҜҸијӣи»ҠиЈЎж’ӯж”ҫи‘—дёҚеҗҢзҡ„е»Јж’ӯжҲ–йҹіжЁӮиҒІпјҢеғҸжҳҜжү“й–Ӣз§Ғдәәзҡ„иҒҶиҒҪдё–з•ҢгҖӮйҖҷ種經驗жҮүи©Іе°ұеғҸжҳҜеңЁжҚ·йҒӢдёҠзӘҒ然間иҒҪиҰӢжүҖжңүдәәиҖіж©ҹиЈЎзҡ„йҹіжЁӮгҖӮдҪҶе…¶еҜҰиҰҒжҳҜеӣһеҲ°еҘҪиҗҠеЎўеҸӨе…ёжҷӮжңҹзҡ„йҢ„йҹіжҠҖиЎ“жЁҷжә–пјҢйҖҷдәӣз’°еўғйҹіжҮүи©Іжңғиў«иҰ–зҲІиҲҮж•ҳдәӢз„Ўй—ңпјҢз”ҡиҮійӮ„жңғз ҙеЈһе°ҚзҷҪжё…жҷ°зҡ„еҷӘйҹіеҗ§гҖӮеӣ жӯӨеҷӘйҹід№ҹжҳҜйҖ еҸҚзҡ„йҖ”еҫ‘пјҢеғҸеҸӨе…ёеҘҪиҗҠеЎўиҮҙ敬зҡ„еҗҢжҷӮпјҢе…¶еҜҰд№ҹжҳҜеҖҹз”ұе°Һжј”зҶұж„ӣзҡ„иҒІйҹіеӘ’жқҗдҫҶжҢ‘жҲ°ж•ҳдәӢеӮізөұжүҖе»әж§Ӣзҡ„еҜ«еҜҰжЁҷжә–гҖӮ
д»ҠеӨ©иҒІйҹіжҠҖиЎ“зҡ„йқ©е‘Ҫд»ҚжҢҒзәҢзҷјз”ҹпјҢиіҰдәҲиҒҪиҰәж–ҮеҢ–ж–°зҡ„ж„Ҹзҫ©пјҢи·іи„«еӮізөұиҰ–иҰәдёӯеҝғжҖқиҖғзҡ„ж„ҹзҹҘ經驗пјҢиҖҢиҒІйҹізҡ„еӘ’д»Ӣзү№жҖ§еңЁж•ёдҪҚжҷӮд»ЈеҸҲжңүжӣҙеӨҡзҷјжҸ®зҡ„еҸҜиғҪжҖ§гҖӮеӣ жӯӨпјҢйӣ»еҪұйҹіжЁӮд№ҹеҸҜд»ҘжҳҜдёҖзЁ®йҹіж•ҲпјҢиғҪжҚ•жҚүз”ҹжҙ»жіҒе‘ізҡ„иҒІйҹҝж•ҲжһңпјҢиҖҢйӣ»еҪұиЈЎзҡ„жӯҢжӣІдёҚеҸӘзӮәж•ҙеҗҲж•ҳдәӢпјҢиҖҢжҳҜд»ҘиҒҪиҰәеҪўејҸжҠ•е°„еҮәзҡ„е…§еҝғж„ҹеҸ—гҖӮиҒІйҹіжҠҖиЎ“её¶дҫҶе·ЁеӨ§зҡ„ж„ҹзҹҘи®Ҡйқ©пјҢд№ҹжҳҜйӣ»еҪұеүөдҪңиҖ…дёҚеҸҜзјәе°‘еүөж–°еӢ•иғҪпјҢд»–еҖ‘еҫһдёҚж»ҝи¶іж–јзҙ”зІ№еҪұеғҸзҡ„иЎЁйҒ”пјҢжӢје‘Ҫең°йҖҸйҒҺиҒІйҹіеҗ‘и§ҖзңҫзҷјеҮәиЁҠжҒҜпјҢиҖҢжғіиҰҒйҖІе…Ҙйӣ»еҪұеүөйҖ зҡ„ж„ҹзҹҘдё–з•ҢпјҢдёҖеҲҮйғҪеҫ—еҫһиҒҪиҰӢй–Ӣе§ӢгҖӮпјҲеҫ…зәҢпјүв–
|
й—ңж–јдҪңиҖ…
зҺӢеҝөиӢұ
е°ұи®Җж–јеңӢз«Ӣеё«зҜ„еӨ§еӯёиӢұж–Үзі»еҚҡеЈ«зҸӯпјҢз•ўжҘӯи«–ж–Үд»Ҙеҗ„зЁ®еӘ’й«”дёӯзҡ„иҒІйҹізӮәдё»йЎҢпјҢж“”д»»гҖҠж”ҫжҳ йҖұе ұгҖӢзү№зҙ„ж’°зЁҝеӨҡе№ҙгҖӮ
|
|
в–Қ延伸й–ұи®Җ
596жңҹгҖҗж”ҫжҳ й ӯжўқгҖ‘
|
|
